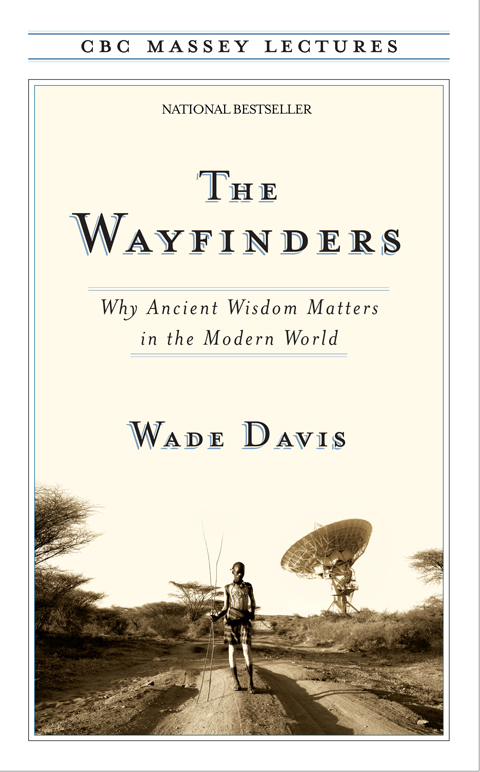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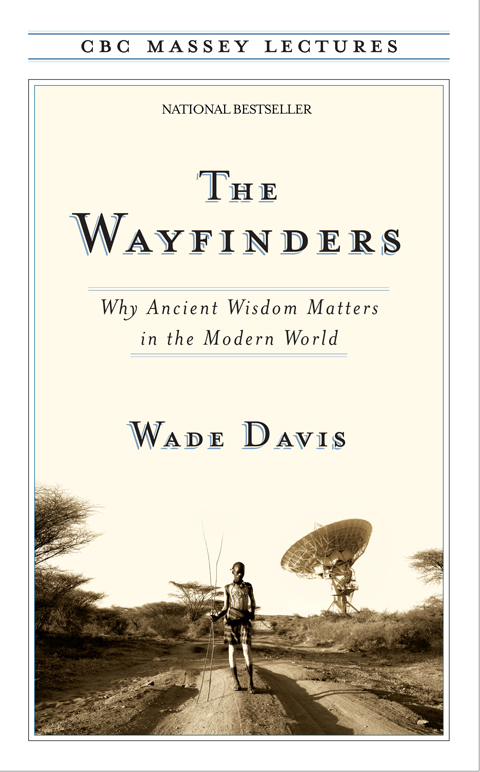
马西讲座由CBC广播电台、阿南西出版社和多伦多大学马西学院共同赞助。该系列讲座是为了纪念加拿大前总督文森特·马西阁下而创立的,于1961年首次举办,旨在为广播电台提供一个论坛,让当代主要思想家能够就我们时代的重要议题发表见解。
本书收录了2009年马西讲座”寻路者”的内容,作为CBC广播电台《思想》系列节目于2009年11月播出。该系列的制作人是菲利普·库尔特;执行制作人是伯尼·卢赫特。
韦德·戴维斯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包括《蛇与彩虹》、《世界边缘的光》、《一条河》和《云豹》。他是一位获奖的人类学家、民族植物学家、电影制作人和摄影师,他的文字和摄影作品曾发表在众多出版物上,包括《环球邮报》、《麦克林》、《新闻周刊》、《国家地理》、《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他目前担任华盛顿特区国家地理学会的驻会探险家,并在该市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两地生活。
古老智慧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

版权所有 © 2009 韦德·戴维斯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包括电子或机械方式、影印、录制或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
未经出版商许可,通过互联网或任何其他方式分发本电子版本是违法的。请不要参与受版权保护材料的电子盗版;请仅购买授权的电子版本。我们感谢您对作者权利的支持。
本版本于2009年出版
阿南西出版社有限公司多伦多士巴丹拿大道110号801室邮编M5V 2K4 电话:416-363-4343 传真:416-363-1017 网址:www.anansi.ca
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出版物编目
戴维斯,韦德寻路者:古老智慧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 / 韦德·戴维斯著。
(CBC马西讲座系列) 电子书ISBN 978-0-88784-969-5
GN366.W33 2009 303.48’2 C2009-903511-1
封面设计:比尔·道格拉斯,The Bang设计工作室

我们感谢加拿大艺术委员会、安大略省艺术委员会以及加拿大政府通过加拿大图书基金对我们出版计划的财政支持。
献给大卫·梅伯里-刘易斯
1929–2007
“我希望所有土地的所有文化都能像风一样自由地吹过我的房子。但我拒绝被任何一种文化吹倒。” ——圣雄甘地
旅行的一大乐趣就是有机会生活在那些没有遗忘古老传统的民族中间,他们仍能在风中感受过去,在被雨水磨光的石头中触摸历史,在植物的苦叶中品味传统。仅仅是知道在亚马逊地区,美洲豹萨满仍在银河之外旅行;因纽特长者的神话仍然充满意义;西藏的佛教徒仍在追求达摩的气息——这就让我们想起人类学的核心启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并非绝对存在,而只是现实的一种模式,是我们特定文化血统在许多代以前成功做出的一套智识和精神选择的结果。
但是,无论我们是与婆罗洲森林中的游牧比南人同行,还是与海地的伏都教信徒,或是与秘鲁安第斯山脉高原的curandero(治疗师),或是与撒哈拉红沙中的塔马谢克caravanseri(商队队长),或是与珠穆朗玛峰坡上的牦牛牧民一起,所有这些民族都教导我们存在着其他选择、其他可能性、其他与地球思考和互动的方式。这个理念只能让我们充满希望。
无数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环绕地球的智识和精神生命网络,它对地球福祉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我们所知的生物圈这一生物生命网络。你可以将这个社会生命网络视为”民族圈”(ethnosphere),这个术语最好定义为:自意识诞生以来,人类想象力所创造的所有思想和直觉、神话和信仰、观念和灵感的总和。民族圈是人类最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梦想的产物,是我们希望的体现,是我们作为一个极富好奇心和惊人适应性的物种的一切以及我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象征。
正如生物圈——生命的生物基质——正因栖息地的破坏和由此导致的动植物物种丧失而遭受严重侵蚀一样,民族圈也在遭受侵蚀,而且速度要快得多。例如,没有生物学家会认为50%的物种正在消亡。然而,这种生物多样性领域最具末日色彩的情景,与我们所知的文化多样性领域最乐观的情景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
关键指标,可以说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就是语言的消失。当然,语言不仅仅是一套语法规则或词汇。它是人类精神的闪光,是每种特定文化的灵魂进入物质世界的载体。每种语言都是心灵的原始森林,思想的分水岭,精神可能性的生态系统。
在今天使用的7000种语言中,有一半已不再教给儿童。实际上,除非有所改变,它们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失。世界上一半的语言正处于灭绝的边缘。想想这一点。还有什么比被静寂包围更孤独的呢,成为你的族人中最后一个说本族语的人,无法传承祖先的智慧或期待后代的希望。这种悲惨命运确实是地球上某个地方大约每两周就会有人面临的困境。平均而言,每两周就有一位长者去世,带着古老语言的最后音节进入坟墓。这真正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将目睹人类一半社会、文化和智力遗产的消失。这是我们时代隐藏的背景。
有些人很天真地问:“如果我们都说同一种语言,世界不是会更美好吗?沟通不是会更容易,让我们更容易相处吗?”我的回答总是:“这是个好主意,但让我们把那种通用语言定为海达语或约鲁巴语、拉科塔语、因纽特语或桑语吧。”突然间人们就感受到无法说母语意味着什么了。我无法想象一个我不能说英语的世界,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语言,它还是我的语言,是我完整身份的表达。但同时,我不希望它像某种文化毒气一样席卷人类的其他声音、世界的其他语言。
当然,语言在历史长河中有生有灭。巴格达的街头不再有人说巴比伦语,意大利的山丘上也不再有人说拉丁语。但生物学类比再次发挥了作用。灭绝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总的来说,在过去6亿年中,物种形成——新生命形式的进化——超过了消失的速度,使世界变得更加多样化。当拉丁语的声音从罗马消失时,它们在罗曼语族中找到了新的表达。今天,正如植物和动物在生物学家认为是史无前例的灭绝浪潮中消失一样,语言也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死亡,以至于它们没有留下任何后代。
生物学家认为也许20%的哺乳动物、11%的鸟类和5%的鱼类受到威胁,植物学家预期将失去10%的植物多样性,而今天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见证着世界现存语言一半即将消失的景象。超过六百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一百人。大约3500种语言仅靠全球人口的0.2%维持生存。相比之下,十种最普遍的语言正在蓬勃发展;它们是人类一半人口的母语。世界人口的80%完全用83种语言中的一种进行交流。但那些诗歌、歌曲和其他声音中编码的知识呢,那些守护和保管着世界98.8%语言多样性的文化呢?一位长者的智慧是否因为他或她只对一个听众交流就不那么重要了?一个民族的价值是否只是其人数的简单相关?恰恰相反,每种文化按定义都是我们家族树上的重要分支,是知识和经验的宝库,如果给予机会,它们是未来灵感和希望的源泉。“当你失去一种语言时,”MIT语言学家肯·黑尔(Ken Hale)在去世前不久说道,“你就失去了一种文化、智力财富、一件艺术品。这就像在卢浮宫投下炸弹一样。”
但究竟什么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有的话,应该对此做些什么?近年来有许多书籍向技术和现代性的全球扫荡致敬,暗示世界是平的,人们不必移民就能创新,我们正在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现实,由特定的经济模式主导,未来可以在任何地方同时找到。当我读这些书时,我只能想到我一定是在与这些作家非常不同的圈子里旅行。正如我希望这些讲座将证明的那样,我有幸了解的世界绝对不是平的。它充满了峰谷、奇特的异常和神圣的干扰。历史并没有停止,文化变化和转型的过程今天仍然像以往一样充满活力。世界只有对那些坚持通过单一文化范式的镜头——他们自己的——来解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人来说才显得单调。对于那些有眼睛看、有心感受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地形图。
从基因学开始庆祝文化和多样性似乎有些不寻常,但这确实是故事的真正起点。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我在国家地理学会的朋友兼同事斯宾塞·威尔斯一直在领导基因地理项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性努力,旨在追踪人类原始旅程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轨迹。他和其他人口遗传学家所发现的是现代科学的重大启示之一。正如斯宾塞提醒我们的,我们是十多亿年进化转变的结果。我们的DNA以四个简单的字母编码,是一份可以追溯到生命起源的历史文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故事中的一个章节,这是一个关于探索和发现的叙述,不仅记录在神话中,也编码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们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被一个奇迹充电——四种分子类型的双螺旋,四个简单的字母A、C、G和T,以复杂的序列相连,帮助协调感知存在的每一次脉动。有六十亿比特的数据被包裹、盘绕并旋转在我们存在的黑暗中。如果将任何人体中的DNA拉伸成一条直线,它不仅能到达月球,还能到达距离地球等距的3000个天体。当然,在生命中,这条链,这种神秘的遗产,被断开并捆绑成四十六条染色体,代代相传。每一次新的结合,每一个新的孩子,这些染色体都会被重新洗牌和重组,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以父母基因禀赋的独特组合出生。
但重要的线索仍然存在。在每个细胞的细胞核中,Y染色体——决定男性性别的因子,大约5000万个核苷酸的片段——或多或少完整地代代相传,从父亲传给儿子。在每个细胞的线粒体(产生能量的细胞器)中,DNA也或多或少完整地代代相传,但是从母亲传给女儿。正因为如此,也仅仅因为如此,这两股DNA链如同时间机器一样,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过去的窗口。
几乎所有人类DNA——三十亿个核苷酸中的99.9%——在人与人之间都没有差异。但在剩余的0.1%中蕴藏着启示,原始代码本身的差异为人类祖先提供了重要线索。在遗传信息的转录和复制过程中,这些数十亿比特的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小故障。本应该是字母A的地方,出现了G。这些是突变,它们时刻在发生。它们并非灾难性的。单个突变很少会导致表型变化。代码中单个字母的转换不会改变皮肤的颜色、身体的高度,更不用说个人的智力和命运了。然而,这种基因漂移确实会被不可磨灭地编码在该个体后代的基因中。这些单一遗传突变是标记,是”接缝和点焊”,正如斯宾塞所写的,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些标记使人口遗传学家能够以一代人前无法想象的精确度重建人类起源和迁徙的故事。通过研究个体间DNA的差异而非相似性,通过追踪标记在时间中的出现,通过观察数千个标记,可以确定血统的世系。两棵缠绕的进化树正在被构建——一棵通过父亲和儿子,另一棵通过母亲和女儿——整个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旅程被带入了非常精确的焦点。
压倒性的科学共识表明,直到大约6万年前,全部人类都生活在非洲。然后,可能是由于气候和生态条件的变化导致非洲草原的沙漠化,一小群男女老幼,可能只有150个个体,走出了古老的大陆,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推动人类散居多波浪潮的因素永远无法完全知晓,尽管推测食物和其他资源需求发挥了主要作用。随着人口增长超出土地承载能力,他们分裂了,一些群体继续前行。DNA记录揭示的是,随着较小群体的分离,他们只携带了原先非洲人口中遗传多样性的一个子集。实际上,科学表明,对于所有人类文化,无论他们最终定居在哪里,遗传多样性都会随着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非洲的距离增加而减少。同样,这些差异并不反映表型。它们并不暗示人类潜力的任何差异。它们只是标记,突出了一种文化的宇宙地图,揭示了我们的祖先何时何地踏上了开放的道路。
第一波迁徙沿着亚洲的海岸线,穿越亚洲的腹地,最早在公元前50,000年到达澳大利亚。第二次迁徙向北穿过中东,然后转向东方,在大约40,000年前再次分化,一支向南进入印度,一支向西南穿过东南亚到达中国南部,另一支向北进入中亚。从这里,从世界最大大陆中心的连绵山脉出发,随后的两次迁徙将人类带到了西边的欧洲(公元前30,000年)和东边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在公元前20,000年就有人居住了。最后,大约12,000年前,就在新的一波迁徙从中东进入东南欧,人们向北穿过中国的时候,一小群猎人穿越了白令陆桥,首次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人类定居点。在2,000年内,他们的后代就到达了火地岛。从非洲的卑微起源开始,经过持续了2,500代人的旅程,这场历时40,000年的大迁徙,我们的物种定居了整个可居住的世界。
在继续之前,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项遗传学研究如此重要,因为这真正为这些讲座中将要讨论的所有主题和问题提供了基础。在我的有生之年,除了阿波罗计划带回的从太空看地球的视角外,没有任何科学发现能像这样将人类精神从自记忆诞生以来就困扰我们的狭隘暴政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名社会anthropologist(人类学家),我接受的训练是相信历史和文化的首要地位,认为它们是人类事务的关键决定因素。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教养,而非天性。人类学最初是试图解读异域他者的尝试,希望通过拥抱不同而新颖的文化可能性的奇迹,我们可以丰富对人性和我们自身人性的欣赏和理解。然而,很早这个学科就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绑架。正如十九世纪的博物学家们试图对造物进行分类,同时应对达尔文启示的冲击,anthropologist(人类学家)们成了王室的仆人,被派遣到帝国的边远地区,任务是了解奇异的部落民族和文化,以便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管理和控制。
从鸟喙、甲虫和藤壶研究中提炼出的进化理论,以对那个时代有用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理论中。正是anthropologist Herbert Spencer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在美国靠非洲奴隶的劳动建设起来,英国阶级制度如此分层以至于富人的孩子平均比穷人的孩子高6英寸的时代,一个为种族和阶级差异提供科学依据的理论是受欢迎的便利工具。
进化意味着随时间的变化,这一点加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改良崇拜,暗示了人类事务的进步,一个从原始到文明、从非洲部落村庄到伦敦和海滨大道辉煌的成功阶梯。世界各种文化被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其中各个社会代表着被捕获并困在时间中的进化时刻,每一个都是通向文明的想象攀登中的一个阶段。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确定性的必然结果是,先进社会有义务帮助落后者,教化野蛮人,这一道德责任再次很好地服务于帝国的需要。“我们恰好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Cecil Rhodes著名地说,“我们居住的世界越多,对人类越好。”印度第十一任总督George Nathaniel Curzon表示同意。“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伟大的东西,”他写道,“如英帝国这样伟大的人类福祉工具。我们必须把所有精力和生命都献给维护它。”当被问及为什么印度政府中没有一个印度本地人时,他回答:“因为在次大陆的3亿人口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确立了种族的首要地位和维多利亚英国的固有优越性后,anthropologist(人类学家)们开始着手证明他们的观点。对人类的科学错误测量始于phrenologist(颅相学家)们用卡尺和尺子检测和记录颅骨形态的微小差异,这些差异被认为反映了智力的先天差异。不久,物理anthropologist(人类学家)们就在世界各地测量和拍摄人们,都基于一个严重缺陷的观念,即仅仅通过比较身体部位、臀部形状、头发质地,以及不可避免的肤色,就能获得我们物种的完整分类。分类学之父林奈在十八世纪晚期确定所有人类都属于同一物种,Homo sapiens,“智慧人”。但他通过区分五个亚种来规避风险,他将它们识别为afer(非洲人)、americanus(美洲原住民)、asiaticus(亚洲人)、europaeus(欧洲人),最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分类单元monstrosus,基本上包括了其他所有人,所有那些在欧洲人眼中如此奇异以至于无法分类的民族。
在林奈(Linnaeus)之后一个多世纪,体质人类学受到对达尔文理论选择性误读的启发,接受了种族概念作为既定事实。确认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成为了学者和探险家议程和职责的一部分。在那些着手描绘种族传奇的人中,有一位英国陆军军官和探险家托马斯·惠芬(Thomas Whiffen)。在橡胶恐怖的高峰期,他沿着哥伦比亚亚马逊地区的普图马约河(Río Putumayo)而下,将森林描述为”天生恶毒,是一个可怕的、极其恶意的敌人。空气中弥漫着腐烂植被缓慢蒸腾腐朽的烟雾。温和的印第安人,和平而慈爱,只是狂热想象的虚构。印第安人天生残忍。“惠芬指出,在他们中间生活一年,就会”因他们的兽性而感到恶心”。在成千上万的博拉(Bora)和惠托托(Huitoto)印第安人遭到奴役和屠杀的时候,他为未来的旅行者提供建议,建议探险队伍限制在不超过25人。“根据这个原则,”他写道,“可以看出,携带的行李数量越少,可用于保证探险安全的步枪数量就越多。”
惠芬的著作《西北亚马逊》(The North-West Amazons)在1915年出版时广为传阅,他声称遇到了食人宴会,“囚犯被吃得一点不剩,野蛮的疯狂节庆…眼神炽热、鼻孔颤动的男人…一种无所不在的狂乱状态。”那个时代的其他学术探险家,尽管稍显克制,但仍然认同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慈善地称之为体质人类学”阴茎学派”的观点。同样沿着死亡之河普图马约河而下的法国人类学家欧金尼奥·罗布雄(Eugenio Robuchon)注意到,“总的来说,惠托托人有着纤细而神经质的肢体。”他著作的另一章开头写道:“惠托托人有着灰铜色皮肤,其色调对应巴黎人类学会色彩量表的29号和30号。”惠芬著作中的一个脚注写道:“罗布雄称女性的乳房呈梨形,照片显示明显的梨形乳房和指状乳头。我发现它们更像球体的一部分,乳晕不突出,乳头呈半球形。”
并非每个人都对测量乳房和头骨感兴趣。那些更愿意展望更光明世界的人歪曲了达尔文理论,期望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优生学意味着”良好的出生”,这个在二十世纪之交蓬勃发展的运动呼吁对健康强壮的个体进行选择性繁殖,目标是改善人类的基因库。到1920年代,这个理想被颠倒为强制绝育和剔除异常的理论依据。如果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善基因库,那么通过从族群中消除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因素,肯定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这就是后来让德国人为屠杀和系统性灭绝数百万无辜民众辩护的扭曲科学原则。
鉴于这段肮脏的历史,颅相学(phrenology)荒谬的野心,优生学杀人的后果,科学界即使在推广最可疑的主张时也表现出的长期自信和傲慢,难怪许多人,尤其是来自非西方传统的人,对任何关于人类起源和迁移的全面理论都保持深度怀疑。这种研究依赖于从偏远和孤立人群中收集和分析人类血液,这只会进一步激化激情和担忧。土著民族特别对以下建议感到深深冒犯:他们在叙事和神话中神圣化的家园,可能并非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由他们的祖先居住。甚至有指控称,最近关于我们遗传传承的科学揭示可能会引发公开冲突,并强制将部落民族从他们实际上在所有活人记忆中都占据的土地上迁移出去。
我相当确信这些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历史表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不需要借口来蹂躏弱者,我不相信从这些新研究中产生的任何理论会以某种方式改变平衡,并且本身就导致一个民族被剥夺权利。确实,纳粹转向关于遗传学和种族的伪科学来为种族灭绝辩护,但是,正如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提醒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被他们关于人性社会可塑性的伪科学幻想激发,犯下了同样卑劣和毁灭性的种族灭绝行为。“对人类的真正威胁,”平克写道,“来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对人权的否认,而非对自然与教养的好奇心。”
知识对文化不构成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努力只产生某种特定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在特定世界观内定义的。西方科学从定义上拒绝对起源神话的字面解释,比如将海达人根植于海达瓜伊的神话。但这种拒绝并不能平息海达人的精神,也不能说服我的朋友古雅奥——海达民族委员会主席——他的人民自从人类从蛤壳中出现、乌鸦从虚无中溜出偷取太阳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个群岛上。科学界已经提出海达人可能”来自别处”的观点;这一直是正统人类学的基础。但这种科学”真理”丝毫不会限制今天海达人的权威和力量。他们与加拿大政府进行国与国对话的能力与神话中的祖先声明关系不大,而与政治力量、接触时占据土地的先验证据,以及古雅奥等领导人在世界范围内为其人民动员支持的能力息息相关。
科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其目的不是产生绝对真理,而是启发我们以越来越好的方式思考现象。直到1965年,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还写了两本书:《种族起源》和《人类的现存种族》,在书中他提出了存在五个不同人类亚种的理论。显然,自林奈时代以来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库恩认为,欧洲人在政治和技术上的主导地位是他们进化的遗传优势的自然结果。他甚至断言”种族混合会破坏一个群体的遗传和社会平衡”。当时库恩是美国体质人类学协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正教授,以及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学馆长。
如此方便的论述——在吉姆·克劳法和种族隔离的最后岁月里——直到1965年还被学术界认真对待,这确实应该让我们在考虑群体遗传学新研究的影响时暂停思考。但当科学实际上表明种族的终结,当它毫无疑问地揭示种族是虚构的时候,我们有义务倾听。我们至少应该希望科学家们这一次是对的。
他们确实是对的。他们毫无疑问地揭示了人类的遗传禀赋是一个单一的连续体。从爱尔兰到日本,从亚马逊到西伯利亚,人群之间没有明显的遗传差异。只有地理梯度。地球上最偏远的社会在其人民中包含了我们总遗传多样性的85%。如果其余的人类被瘟疫或战争席卷而去,瓦欧拉尼人或巴拉萨纳人,伦迪莱人或图阿雷格人都会在他们的血液中拥有全人类的遗传禀赋。就像精神和心灵的神圣宝库一样,这7000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都能提供种子,让人类的所有多样性得以重生。
所有这些意味着生物学家和群体遗传学家终于证明了哲学家们一直梦想的真理:我们都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是用同样的遗传布料裁剪而成的。
因此,根据定义,所有文化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心智敏锐度,相同的原始天赋。这种智力能力和潜力是否通过令人惊叹的技术创新作品得到发挥——这是西方的伟大成就——还是通过解开神话中固有的复杂记忆线索——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主要关注点——这只是选择和取向、适应性洞察和文化优先级的问题。
在文化史上没有进步的等级制度,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成功阶梯。维多利亚时代关于野蛮和文明的观念——欧洲工业社会自豪地坐在进步金字塔的顶端,底部扩展到世界上所谓的原始人——已经被彻底推翻,实际上因其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自负而在科学上受到嘲笑。科学研究的辉煌和现代遗传学的启示以惊人的方式确认了人类本质上的连通性。我们共享神圣的禀赋,共同的历史写在我们的骨头里。正如这些讲座将要表明的,世界上无数的文化不是现代性的失败尝试,更不是成为我们的失败尝试。它们是人类想象力和心灵的独特表达,是对一个根本问题的独特回答:作为人类活着意味着什么?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世界各地的文化用7000种不同的声音回应,这些声音共同构成了我们人类应对未来2500代将面临的所有挑战的资源库,即使我们继续这永无止境的旅程。
但是这些数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是谁呢?他们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能通过遗传标记追踪他们随后的旅程,那么应该有可能找到一个仍然生活在非洲的民族,一个从未离开过的民族,因此他们的DNA缺乏所有那些在我们祖先遍布世界各地的连续浪潮中发生的突变证据。正如斯宾塞·韦尔斯的研究再次强调的那样,这样一个民族确实已经被确认,他们是一个几十年来让人类学家着迷的文化群体。如今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炽热沙丘中,55,000人分散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安哥拉约8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桑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曾经居住在整个次大陆和东非大部分地区的民族的后裔。被一波又一波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所取代,桑人作为布须曼人幸存下来,他们是游牧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精确而严格的知识使他们的民族能够独自在地球上最严酷和最贫瘠的沙漠景观之一中生存。这一非凡的适应性信息体系,这一智力工具箱,编码在他们母语的词汇和声音中,这是一种语言学奇迹,一种与任何其他已知语言家族完全无关的语言。在日常英语中我们使用31种声音。桑人的语言有141种,这是一种韵律和咔嗒声的嘈杂组合,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这回响着语言的诞生。确实,基因数据表明可能就是这样。关键标记的缺失表明桑人是人类家族树中的第一批人。如果爱尔兰人和拉科塔人,夏威夷人和玛雅人是枝条和肢体,那么桑人就是树干,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当我们其余的人决定旅行时,桑人选择留在家里。
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当酒精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发展的虚假和扭曲承诺,粉碎了他们许多人的生活之前,桑人遵循着他们自然世界的节奏大约有10,000年。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他们预测季节每一个细微差别、动物每一个动作、植物生长时发出的声音的能力。水是持续的挑战。在卡拉哈里,一年中有十个月没有地表水。水必须在树洞中找到,用空心芦苇从泥土下吸取,或储存在鸵鸟蛋中,用草塞住并标记上主人的记号。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唯一的水源是从根部找到的液体或从动物内脏中挤出的液体。
在旱季,从五月到十二月底,桑人不断迁移。虽然他们主要认为自己是狩猎者,但他们通过吃植物生存,每个成年人每天要消耗5公斤野生甜瓜。当甜瓜枯萎时,桑人发现他们必须挖掘,在身体每天因出汗失去3升水的沙漠环境中,需要超过二十个从沙子中挖出的大块茎才能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在最糟糕的月份,棕色土狼的季节,桑人在地上刮出凹坑,用尿液润湿土壤,然后完全静止地躺在撒了一层沙子的下面,被苍蝇折磨着,等待白天的酷热过去。太阳不是生命的源泉,而是死亡的象征。最大匮乏的时期也是希望的时期,因为十月开始小雨季,第一批调皮的雨滴预示着干旱期的结束。从十月到十二月的三个月里,大地被这种雨水的承诺折磨着,而这从来都不够。那些幸运地生活在永久水源附近的人聚集在小营地里。大多数人在黄昏和黎明觅食寻找根茎。酷热持续,干燥的风吹过棕色草原,死者的灵魂以尘卷风的形式出现,在灰黄色的地平线上旋转。
最后,一月雨季到来,三个月里人们庆祝重生和再生的季节。但在卡拉哈里,雨水仍然是相对的。有时云层聚集成巨大的雷暴云,劈开天空,在一小时内用8厘米的雨水猛烈冲击大地。但也有些年份雨水根本不来,整个雨季的降水量只有5厘米。人们必须在地表下挖掘几米深才能到达不透水层,那里有时可能找到水。即使在雨季,渴死的可能性也是持续存在的。
在好年景里,雨水带来相对的丰盛。沙地上形成水池,仅仅装备着挖掘棒、收集袋、编织网和鸵鸟蛋壳来装水,人们以小群体形式迁移,这些大家庭单位偶尔会聚集成更大的群体来庆祝水果或种子的收获,以及猎物的出现。这些游荡不是随机的。每一段路程都穿越已知的土地,这些历史悠久的领地充满着叙述,每一个都授予一群人对特定资源的所有权——这个资源可能是一棵树或灌木,或者是公认的蜂蜜来源,这是最珍贵的甘露。蜜蜂之母是创造万物的伟大之神的妻子。蜂蜜的源泉受到名字的保护,侵犯他人权利是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
最喜欢的季节是四月,猎人的季节。虽然植物构成了桑族饮食的主体,但肉类是最受渴望的食物,因为正是狩猎将男孩转变为男人。在大多数年份里,到了四月,雨水驱散了酷热,而沙漠冬季的严寒尚未到来。到处都有成熟的食物——地下、藤蔓上、每棵树和灌木的每根枝条上。羚羊产下幼崽后,肥壮而众多。领域被遗忘,男人们以小型狩猎队的形式在沙漠中游走,一天步行远达60公里,每晚回到篝火和家人身边。他们轻装上阵:短弓和用树皮制成、以猎物阴囊为箭头的箭囊;生火棒;用于吸水的空心芦苇;刀和短矛;用于修补的植物胶块;用于将肉串在火上的尖棍。
桑族男人团队狩猎,观察迹象。没有什么能逃过他们的注意:草叶的弯曲、折断树枝的拉力方向、足迹的深度、形状和状况。一切都写在沙子里。桑族的通奸是一个挑战,因为每个人的脚印都是可识别的。从单一的动物足迹,桑族猎人可以辨别方向、时间和行进速度。凭借机智,在与豹子和狮子等严重掠食者的直接竞争中生存,他们成功猎杀了令人惊叹的各种生物。他们用毒桩陷阱来捕捉河马。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跟在大象脚后,用斧头的迅速一击切断这些巨大动物的脚筋。在狮子的猎物附近徘徊,他们等到动物吃饱,然后将迟缓的猫科动物从死尸旁赶走。鸟类用网在飞行中被捕获。羚羊被字面意义上追到地面,通常需要几天时间。桑族的弓很短,力量有限,有效射程约25米。箭很少穿透猎物。它们划破皮肤,但通常这就足够了,因为箭头涂有致命毒素,这些毒素来自两种甲虫的幼虫,这些甲虫以沙漠树木Commiphora africana的叶子为食。桑族在群落中寻找甲虫,挖掘茧,将其储存在羚羊角制成的容器中。他们在手指间来回滚动幼虫,软化内部而不破坏皮肤。然后挤压它们以渗出糊状物。经过阳光晾干,这种毒液一旦注入血液,就会引起痉挛、瘫痪和死亡。
狩猎是将我们带入桑族生活核心的隐喻。不狩猎的男人仍然是孩子。要结婚,男人必须向新娘的父母带来肉食。第一次猎杀羚羊是青春的高潮,这一时刻被父亲永远记录在猎人的皮肤上,父亲用骨头做浅切口,将肉和脂肪的混合物揉进伤口,如果猎杀的是公鹿就在身体右侧留疤,如果是母鹿就在左侧。纹身用猎人之心标记男孩——这是魔力的强大源泉,因为桑族不只是杀死猎物。他们与猎物进行舞蹈,一种仪式性交换,最终以生物字面意义上献出自己作为供品和牺牲而结束。每次狩猎都以精疲力竭结束,因为羚羊意识到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逃脱人类的追捕。然后它停下来转身,箭矢飞出。
大型猎物的肉在营地的所有成员间分享,分配不是由猎人决定,而是由箭的主人决定。桑族男人总是互相赠送箭矢。箭矢,带着骨制箭头、优雅的箭杆、毒药的完美混合,代表着桑族技术的最高成就。但它的力量在于社会领域,因为每次箭矢的交换都建立了互惠的纽带,锻造了桑族生活的团结。拒绝礼物是敌意行为。接受意味着承认连接和义务。箭矢代表的远不止必须通过贸易兑现或随时间偿还的债务。相反,它确保了终身的义务,将个人与更大的社会领域结合起来,将青年带入猎人的领域,将猎人带入炉边和神圣之火的圈子。
如果桑族将太阳与死亡联系起来,火象征着生命、人民的团结、家庭的生存。礼物肉品正式化了女人的订婚,而离婚则在她简单回到家庭火堆的那一刻正式化。母亲在黑暗中分娩,通过重新进入火光圈宣布分娩。当长者变得太老太弱无法与人民继续前行时,他被留下等死,由荆棘丛的圈子和脚边的火保护,免受鬣狗伤害,火光照亮他通往下一个世界的路。对桑族来说有两个伟大的灵魂:东方天空的伟大之神;以及西方的次要之神,负面和黑暗的源泉,死者的看护人。为了抵御西方之神,偏转疾病和不幸的箭矢,桑族围绕火堆跳舞,将自己投入恍惚状态。居住在腹部的生命力作为蒸汽沿着脊柱上升,触及颅骨底部,扩散到全身,将精神旋转到更高的意识中。治疗舞蹈以猎人围绕火堆结束,他们通过将自己的头放入燃烧的煤炭中来戏弄火焰和众神。
语言、隐秘、精神,适应性天赋——这些是桑人(San)在卡拉哈里沙漠生存的工具。这些大概也是我们远古祖先从非洲带出的特质。但今天桑人的民族志描绘,或者现代殖民主义破坏之前桑人的生活方式,仍然给我们留下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回溯时光,触及这些大地漫游者的本质,这些找到通往地球上每个宜居之地的祖先存在?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如何思考?除了维持生存的原始挑战之外,什么激励了他们?什么点燃了——正如我的好友诗人克莱顿·埃什勒曼(Clayton Eshleman)如此美妙地询问的——想象力的”杜松引线”(juniper fuse),因为这必定标志着人类起源的真正时刻,导致文化创造的意识展开。在某个时刻,一切都开始了。
我们知道人族谱系在非洲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最早的骨骼遗骸是2006年古人类学家泽雷塞奈·阿莱姆塞格德(Zeresenay Alemseged)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沙漠发现的一个三岁女孩。他将她命名为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以她被发现的地方命名,她的骨骼在那里安息了330万年。我们自己的物种智人(Homo sapiens)直到仅仅20万年前才进化出现。我们有直接的竞争者。人类人口起伏波动,在某个关键时刻我们几乎灭绝,也许减少到一千个个体。但某种东西把我们从灭绝中拯救了回来。
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与人族树上另一个分支共享世界,我们的远房表亲尼安德特人,他们是同一祖先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后代。尼安德特人显然有意识。他们使用工具,有证据表明早在7万年前就有故意埋葬的行为。但无论是大脑尺寸的增加、语言的发展,还是某种其他进化催化剂,我们的物种拥有竞争优势,最终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启动了其命运,智力的爆发让尼安德特人在生存中喘息挣扎。
见证这一原始精神闪光的地方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地下,以及比利牛斯山脉之外的西班牙。当尼安德特人生活的最后痕迹在2.7万年前从欧洲消失时,由我们直系祖先创造的令人震撼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艺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深入地下,穿过狭窄的通道,进入由兽脂灯闪烁照明的洞室,男男女女以stark现实主义绘制他们崇敬的动物,单独或成群,利用石头的轮廓使形式如此戏剧性地生动起来,整个洞穴至今仍因早已灭绝的生物而生机勃勃。
在肖维(Chauvet)和阿尔塔米拉(Altamira),以及后来的拉斯科(Lascaux)和佩什·梅勒(Pech Merle)等遗址发现的具象艺术的精细程度令人惊异,不仅因为其超越性的美,也因为它告诉我们,一旦被文化激发,人类潜能的开花是何等壮观。技术技能,对红赭石(red ochre)和黑锰、氧化铁和木炭的利用,产生完整的色彩调色板,脚手架的使用,应用颜料的多样技术,这些本身就令人瞩目,表明相对高水平的社会组织和专门化,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包的天才中得到呼应,那些从燧石敲击而成的优雅刮削器和刀片。负空间和阴影的使用,构图和透视感,动物形式在时间中的叠加,表明高度进化的艺术美学,这本身暗示着某种更深层渴望的表达。
我最近与克莱顿·埃什勒曼在法国多尔多涅(Dordogne)度过了一个月,他研究洞穴艺术已经三十多年,自从1974年春天一个宿命的早晨,他放弃了——如他所说——鸟鸣和蓝天的世界,进入一个限制性黑暗的领域,这个领域让他的存在充满了”神秘的热情”。像他之前的许多观察者一样,他不仅被所看到的而且被在洞穴感官隔离中的感受所眩惑和困惑,他的想象悬浮在意识和一个吞噬一切的大地灵魂之间,一个”活生生的、深不可测的心理力量储藏库”。他不仅关注岩石上描绘的内容,也关注缺失的内容——野牛和马是最常描绘的动物,而食肉动物代表最少。图像孤立地漂浮;没有背景或地面线。对人的描绘很少,没有战斗场面,没有狩猎场景,没有身体冲突的表现。
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徒劳地努力为这些作品分配目的。“我们可以添加诸如宗教和魔法这样的词,”他写道,“但事实仍然是,所涉及动机的复杂性、紧迫性和纯粹的巨大力量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更不用说重新捕捉了。”弗莱将描绘的动物视为”人类意识和力量向他们[人类]在周围世界中能看到的最大能量和力量对象的某种延伸”。就好像在将这些形式绘制到岩石上时,艺术家以某种方式同化了”潜藏在自然中的能量、美和难以捉摸的荣耀到观察的心灵中”。我们用人类的眼睛看动物形式,“怀疑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一个通过穿上动物皮肤而与动物认同的巫师或萨满”。
Clayton也感觉到,洞穴艺术所做的远不止是唤起狩猎的魔力。他认为,人类曾经具有动物本性,然后在某个时刻,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人类不再是动物了。这些艺术向那个时刻致敬——人类通过意识将自己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成为我们现在所知的独特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Clayton所写的,这些艺术几乎可以被视为”怀旧的明信片”,是对动物和人类曾经合一的失落时代的哀叹。原始萨满教(Proto-shamanism),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精神冲动,其发展是为了通过仪式来调和甚至重新建立这种不可逆转的分离。也许最令人瞩目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的基本要素在长达2万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不变,这个时间跨度是今天的我们与吉萨大金字塔建造者之间时间距离的五倍。如果这些是怀旧的明信片,那么我们的告别确实是非常漫长的。
洞穴艺术也标志着我们不满情绪的开始,标志着对意义和理解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从那时起就推动着人类的梦想。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过去5万年中的整个存在体验可以浓缩为两个词:如何和为什么。这些是所有探究的出发点,是文化围绕其结晶的洞察碎片。
所有民族都面临着相同的适应性要求。我们都必须生育;抚养、教育和保护我们的孩子;在长者步入人生最后阶段时安慰他们。几乎所有文化都会赞同《十诫》的大部分信条,这并不是因为犹太世界具有独特的灵感,而是因为它阐述了允许社会性物种繁荣发展的规则。很少有社会不禁止谋杀或盗窃。所有社会都创造传统,为配偶关系和生育带来一致性。每种文化都尊重其死者,即使它们在努力理解死亡所暗示的不可避免分离的意义。
面对这些共同挑战,文化适应的范围和多样性令人惊叹。狩猎采集社会从东南亚和亚马逊的雨林到澳大利亚干燥平坦的沙漠都有繁荣发展;从喀拉哈里沙漠到北极高纬度偏远冰冷的地区;从美洲广阔的平原到巴塔哥尼亚的潘帕斯草原。旅行者和渔民已经定居在世界各大洋几乎每一个岛链上。复杂的社会仅仅建立在海洋的恩赐之上——鲑鱼、eulachon和鲱鱼为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第一民族带来了生命。
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革命中,人类开始驯化植物和动物。游牧民族定居在地球的边缘地带:撒哈拉沙漠的沙地、青藏高原和亚洲草原的狂风扫荡地带。农业家们选取了少数几种草类——小麦、大麦、水稻、燕麦、小米和玉米——从它们的丰收中产生了剩余,可以储存的食物,从而允许等级制度、专业化和定居生活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传统定义的文明标志。伟大的城市兴起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王国、帝国和民族国家。
没有任何系列讲座能够充分展现人类文化体验的全部奇迹。文化这个词本身就难以精确定义,即使这个概念包含了众多内容。新几内亚山区几百名男女组成的小而孤立的社会有其自己的文化,但爱尔兰和法国等国家也是如此。不同的文化可能分享相似的精神信仰——实际上,这在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启发的土地上是常态。虽然语言通常倾向于描绘独特的世界观,但例如在阿拉斯加,有些民族已经失去了用母语说话的能力,但仍然保持着充满活力的文化意识。
也许我们能够接近文化有意义定义的最近方式是承认,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特且不断变化的星座,我们通过观察和研究其语言、宗教、社会和经济组织、装饰艺术、故事、神话、仪式实践和信仰,以及大量其他适应性特征和特点来识别它。文化的全面衡量既包括一个民族的行动,也包括他们愿望的品质,以及推动他们生活的隐喻的本质。对一个民族的描述如果不涉及他们家园的特征——他们决定在其中度过命运的生态和地理基质——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正如景观定义性格一样,文化源于地方精神。
在这些讲座的过程中,我期待着与你们一起探索其中的一些世界。我们将前往玻利尼西亚,颂扬那种使寻路者能够用他们的想象力和天赋充满整个太平洋的航海艺术。在亚马逊流域,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真正失落文明的后裔——蟒蛇民族,这是一个由神话祖先启发的文化复合体,至今仍在指导人类如何在森林中生存。在安第斯山脉和哥伦比亚圣马尔塔雪山山脉,我们将发现地球真的是活着的,跳动着,以千种方式回应着人类的精神准备。梦境时光和歌唱路线将引领我们到达阿纳姆地的白千层森林,当我们试图理解第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类——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微妙哲学时。在尼泊尔,一条石径将带我们到一扇门前,门将打开,显露出一位智慧英雄、一位菩萨的光辉面容——泽参阿尼,一位45年前进入终身静修的佛教尼姑。犀鸟的飞翔,就像大自然的草体字,将让我们知道我们终于到达了婆罗洲高地森林中的游牧本南人中间。
最终我们在这次旅程中将发现的,将成为下个世纪的使命。地球上燃烧着一把火,带走了植物和动物、古老的技艺和先见性的智慧。面临危险的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档案,一个想象力的目录,一种由无数长者和治疗师、战士、农民、渔民、助产士、诗人和圣人的记忆组成的口传和书面语言——简而言之,人类经验的完整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艺术、智力和精神表达。扑灭这一火焰,这一蔓延的地狱之火,重新发现对人类精神多样性的新认识,正如文化所表达的那样,是我们时代的核心挑战之一。
“这就是我们航行的原因。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长并为自己是谁而自豪。我们通过重新连接我们的祖先来治愈我们的灵魂。当我们航行时,我们在古老故事的传统中创造新的故事,我们实际上是在从古老中创造新的文化。”——奈诺阿·汤普森
让我们暂时滑入由人类想象力带来的最大文化圈。玻利尼西亚:250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地球表面的五分之一,成千上万的岛屿像珠宝一样散布在南海上。几个月前,我有幸与好友奈诺阿·汤普森和玻利尼西亚航海协会一起,在霍库莱阿号上参加训练任务,这是一艘美丽而标志性的船只,以大角星——夏威夷的神圣星辰——命名。作为古代玻利尼西亚伟大航海独木舟的复制品,霍库莱阿号是一艘双体开放甲板双体船,长62英尺,宽19英尺,由约8公里长的绳索绑扎在一起,满载排水量约24000磅。自1975年首次下水以来,霍库莱阿号已横跨太平洋,在大约15万公里的航程中几乎访问了玻利尼西亚三角的每个岛群,从夏威夷到塔希提到库克群岛,再到奥特亚罗瓦或新西兰,东到马克萨斯群岛,南到东至拉帕努伊或复活节岛。更远的航程甚至带她到达了阿拉斯加海岸和日本海岸。霍库莱阿号载有十名船员,包括船长和寻路者,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船上没有一个现代导航设备,除了一台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无线电。没有六分仪,没有深度计,没有GPS,没有应答器。只有航海者的多重感官、船员的知识,以及一个重生民族的骄傲、权威和力量。
当欧洲船员在十六世纪首次进入太平洋时,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星球。在西班牙人中,不是科尔特斯,而是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首先静静地站在达连的一座山峰上,用鹰眼”惊奇地”凝视着一片如此广阔的海洋,它使西方诸岛、荷马的黄金王国和所有”美好的国家和王国”都相形见绌。诗人约翰·济慈在两个世纪后写道,怀着敬畏想象着第一批西班牙人一定感受到的心情。费迪南德·麦哲伦在1520年花了三十八天绕过合恩角——南美洲的南端,一半的人死亡后,滑入了一个他认为是平静海洋的空虚中。他继续航行,在海上四个月,幸存的船员一天天死去,他设法错过了太平洋中的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岛群。最终在1521年4月7日,他在我们现在所知的菲律宾的宿雾岛登陆。麦哲伦是一个勇敢的人,在许多方面都很无情,但也很顽固。在他的绝望和盲目中,他偶然绕过了一个可能在开阔水域教会他很多东西的整个文明。
玻利尼西亚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第一次持续接触发生在三代人之后,1595年阿尔瓦罗·德·门达尼亚·德·内拉跟随东风信风,遇到了一个由十个火山岛组成的群岛,像哨兵一样从赤道海中升起。甚至在登陆之前,他就以他的赞助人、当时的秘鲁总督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卡涅特侯爵的名字将它们命名为马克萨斯群岛。它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孤立的岛群,然而当时却是多达30万人的家园,他们知道自己的岛屿为Te Henua、Te Enata——“人的土地”。
这是一次非凡的文明相遇。马克萨斯人认为他们的岛屿是世界的尽头,是一段神话之旅的最后一站,这段旅程载着他们的祖先沿着风浪从西方而来。每个人都是蒂基(Tiki)——第一个人类——的后裔,每个氏族都能追溯其族谱历史到那次从夕阳之地而来的原始大迁徙。地平线东方是来世之地,灵魂在那里脱离肉体投入大海。因此,对马克萨斯人来说,西班牙人就像恶魔,是在遥远东方天空尽头之外诞生的邪恶化身。肉欲而虚诈,残酷得毫无理由,西班牙人什么都不能提供。他们没有技能,没有食物或女人,甚至不了解自然界最基本的要素。他们的财富只在于所拥有的东西——奇怪的金属物品,并非毫无趣味。但他们不理解真正的财富在于声望,地位只能授予那些能够获得社会债务并将多余食物分配给需要者的人,从而保证免于匮乏。这些白色阿图阿(Atua)——这些来自所有海岸之外的陌生人——在生命秩序中没有位置。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此彻底,以至于巫术对他们无效,甚至祭司的力量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无知如此彻底,以至于不区分平民和酋长,尽管他们以凶残的蔑视对待两者。
西班牙人则被这个岛屿民族困惑,他们似乎既温和又残酷,经常在同一时刻表现出这两种特质。这些伟大的战士完全有能力进行无情的暴力。然而他们的冲突是季节性的、预想的、有计划的和仪式化的。一个人的死亡就能标志着战斗的结束。马克萨斯人没有时间观念,没有罪恶或羞耻的概念。他们的年轻女子炫耀美貌,公开展示性感,然而当西班牙人像任何正常男人那样在公共场所大小便时,她们却感到丑闻和厌恶。如果说性放纵让人兴奋和困惑,那么食人和人祭就令人恐惧,一夫多妻制和tapu——这个土著神奇规则和制裁体系后来产生了禁忌概念——的不可理喻的非理性也是如此。然而野蛮的其他迹象是发光的蓝黑色纹身,覆盖了马克萨斯男性身体腰部和膝盖之间的每个部分,包括生殖器最敏感的表面。
对西班牙人来说,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如此原始的民族怎么能成就如此之多。整个山坡和河谷都被巨大的石头梯田、灌溉渠道和大型平台驯化,数千人可以聚集在那里举行仪式活动、盛宴和庆典,标志着战争的结束或酋长的即位。在这样的时刻,一个祭司会背诵整个世界的神话历史,数百行神圣诗句保存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如果他在任何一个短语上犹豫或结巴,他就必须重新开始,因为这些话语定义了历史的轮廓,也预示着未来的希望。平台周围伸展着翠绿的芋头和山药田,露兜树和椰子。生命之树是面包果,马克萨斯人在凉爽的土地中建造了巨大的石坑,大量淀粉食物可以在厌氧条件下储存,八个月的供应随时储备,这样人们即使在最可怕和最具破坏性的台风中也能生存。
西班牙远征队副指挥官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奎罗斯(Pedro Fernández de Queirós)得出结论,他和同伴们在海滩上遇到的当地人不可能对如此深深印在土地上的文明负责。他注意到当地女性像鱼一样围绕着西班牙船只,因为tapu禁止她们使用独木舟。一个没有运输女性手段的文化怎么能在距离西班牙领土最近前哨三个月航程的一串岛屿上定居?没有磁罗盘好处的男人——他注意到他们缺乏这个——怎么能航行到这些岛屿?他将神话与地理学混为一谈,得出结论马克萨斯群岛实际上是一个巨大南方大陆的前哨,人们被一个仍等待发现的古代文明运输到这些岛屿上。因此,在登陆后的一个月内,西班牙人继续航行到太平洋,寻找这片传说中的土地,这个徒劳的探索将消耗费尔南德斯·德·奎罗斯余生。
在欧洲运输船缺乏测量经度的导航仪器、因恐惧公海而紧贴大陆海岸线航行的时代,关于奇特船只船队在太平洋开阔水域航行的报告陆续传回巴黎和阿姆斯特丹。1616年,一艘荷兰海军舰艇在汤加和萨摩亚之间航行时遇到了一支由巨大远洋贸易独木舟组成的船队。1714年,当伦敦的一座豪宅可以用一百英镑完全装修时,英国政府通过议会法案向任何能够解决确定经度问题的人提供2万英镑的奖金。在精密计时器发明之前,导航员依靠推算航行,这使得普通船只在陆地视线之外航行变得危险。然而在太平洋正在发生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
詹姆斯·库克船长,可以说是皇家海军历史上最出色的航海家,是第一个对此予以认真关注的人。当他登陆夏威夷时,他的旗舰遭遇了一支由3000艘土著独木舟组成的船队。在汤加,他观察到当地的双体船能在他的船行驶两里格的时间内行驶三里格。他遇到了来自马克萨斯群岛的人,他们能够理解大溪地人的语言,尽管这些岛屿相距近1600公里。在1769年他的首次航行中,他在大溪地遇到了一位航海家兼祭司图帕伊亚(Tupaia),后者凭记忆绘制了波利尼西亚除夏威夷和新西兰以外所有主要岛群的地图。超过120块石头被放置在沙滩上,每一块都象征着横跨4000多公里范围内的一座岛屿,从东部的马克萨斯群岛到西部的斐济,这一距离相当于美国大陆的宽度。图帕伊亚后来与库克一起从大溪地航行到新西兰,这是一次近13000公里的迂回旅程,航行范围在南纬48度到北纬4度之间。库克报告说,令他惊讶的是,这位波利尼西亚航海家能够在航行的每一刻都准确指出返回大溪地的确切方向,尽管他既没有六分仪的帮助,也不懂海图。
库克和他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都学会了大溪地语,他们认识到这些遥远岛屿之间明显的文化联系。语言学证据向班克斯表明,太平洋的人民起源于东印度群岛。库克也确信波利尼西亚的定居是从西方开始的。从图帕伊亚那里,他学到了风的某些秘密,如何白天跟随太阳、夜晚跟随星辰,当这位航海家详细描述从大溪地到萨摩亚和斐济、南到澳大利亚、东至马克萨斯群岛的航行方向时,库克印象深刻。但他始终无法完全说服自己这些航行是有目的的。他了解太平洋的狂暴,并且遇到过一群大溪地人,他们在逆风面前无助,偏离航道数百公里,结果在库克群岛搁浅数月。
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在海上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争论。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如何穿越大洋到达这些极其偏远和孤立的土地的?1832年,法国探险家迪蒙·迪尔维尔(Dumont d’Urville)将太平洋民族分为三类。密克罗尼西亚人居住在赤道以北西太平洋的小环礁上。美拉尼西亚人居住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的”黑岛”上。波利尼西亚包括剩余的部分,即东太平洋的”众多岛屿”。以岛屿大小命名的密克罗尼西亚和以居民肤色命名的美拉尼西亚都是任意的称谓。尽管没有历史或民族志的依据,这些称谓至今仍在使用。但在区分波利尼西亚人时,迪蒙·迪尔维尔认识到每个船长日志都记录的事实:实际上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领域,具有密切相关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视野,遍布整个大洋,最极端的两点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加拿大宽度的两倍。波利尼西亚人占据了这些岛屿是不言而喻的。对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解释体现了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说的历史是学究们的骗局这一观点。
早在1803年,西班牙神父华金·马丁内斯·德·苏尼加(Joaquín Martinez de Zuniga)驻扎在菲律宾,他引用向东航行对抗盛行风的不可能性,确定南美洲是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地。稍后,约翰·朗(John Lang),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殖民地早期的一位有影响力的牧师,首次提出了”偶然漂流”的概念,承认波利尼西亚人从西方定居这些岛屿,但仅仅是偶然,是被吹离航线的倒霉船员,是出海寻找食物却偶然发现新土地的渔民。这种偶然传播的概念违背了逻辑——毕竟,哪个渔民会带着他的整套家用工具、鸡、猪、狗、芋头、香蕉、山药,更不用说他的家人——但作为一种解释,它有一个便利之处:承认历史事实的同时否认波利尼西亚人我们现在知道的他们最伟大的成就。偶然漂流理论,特别是由新西兰公务员安德鲁·夏普(Andrew Sharp)所倡导,直到1970年代初才被搁置,当时一系列基于海军水文记录的风向和洋流的复杂计算机模拟得出结论:在从东波利尼西亚各点出发的16000次模拟漂流航行中,没有一次成功到达夏威夷。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水域被两个人进一步搅浑了,他们两人都不是按世界的本来面目看待世界,而是按照他们希望的样子来看待世界。彼得·巴克爵士出生时名为Te Rangi Hiroa,是毛利族母亲和爱尔兰父亲的儿子。作为二十世纪中叶最杰出的波利尼西亚学者之一,他多年来担任檀香山主教博物馆的馆长,并因此在耶鲁大学担任有影响力的教授职位。由于对自己混合血统的敏感,并且在吉姆·克劳法时代急于将波利尼西亚人与”黑人种族”区分开来,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太平洋是由来自亚洲的一波有意迁移浪潮定居的,这一浪潮席卷了各个岛屿,但完全绕过了美拉尼西亚。尽管这与地理情况相矛盾,也忽略了几乎所有波利尼西亚农作物都来自美拉尼西亚的事实,但这确实允许巴克声称:“太平洋的航海大师一定是欧罗巴人种,因为他们没有黑人种族的卷发、黑皮肤和细小腿的特征,也没有蒙古人种的扁脸、矮身材和下垂内眼角的特征。”
如果彼得·巴克的种族不确定性扭曲了他对历史的视角,那么年轻的挪威动物学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则用一个声明颠倒了历史本身,他声称——并以乘坐巴尔沙木筏进行约7000公里的惊险旅程为支撑——波利尼西亚实际上是从南美洲定居的。当这艘名为康-提基号的木筏在1947年8月7日,经过从秘鲁出发的101天航程后,撞上土阿莫土群岛中距离塔希提岛东北约800公里的拉罗亚环礁的礁石时,一位National Geographic英雄诞生了。海尔达尔金发碧眼、相貌英俊、被阳光晒成古铜色、富有魅力且极其上镜:完全是现代冒险家的原型。然而,他支持太平洋人民起源于美洲的论点却极其可疑。
这一论点基于三个非证据的方面。首先,海尔达尔坚持认为,就像早期的西班牙人一样,波利尼西亚人不可能向东航行对抗盛行的赤道风。这是一个古老的谜题,实际上已经被库克船长在与领航员图帕亚(Tupaia)的对话中解决了。答案在波利尼西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也许海尔达尔不知道,或者至少对他的假设来说不太方便。每年都有一个时期贸易风会逆转,航海者可以自由地向东航行,他们完全知道如果迷路了,只需等待回归的东风将他们带回家。
海尔达尔的第二个论点集中在纪念性建筑上。他比较印加人的石工技术与波利尼西亚的石工技术,所引用的相似性如此表面化,对于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来说毫无意义。第三,也是唯一有趣的可能性,是波利尼西亚存在番薯(Ipomoea batatas),这无疑是美洲起源的植物。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只能说明波利尼西亚船只到达了南美洲并返回家园,这一事实得到了最近在智利南海岸埃尔阿雷纳尔(El Arenal)前哥伦布时期垃圾堆中发现鸡骨头(一种亚洲起源的鸟类)的证实。
在提出他耸人听闻的声明时,托尔·海尔达尔忽略了大量的语言学、民族志和民族植物学证据,如今这些证据还得到了基因和考古数据的补充,表明他显然是错误的。他没有注意到,为了让康-提基号在航程开始时越过洪堡德海流,他需要秘鲁海军的帮助。或者在他的时代或今天都没有证据表明,木筏上装配的帆的设计在前哥伦布时期的南美洲就存在。实际上,海尔达尔对解释如此松散,对年代学如此随意,以至于他的理论,正如一位学者所建议的,等同于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声称:“美洲是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天被亨利八世国王发现的,他为无知的土著人带来了福特雷鸟汽车。”但这些都不重要。海尔达尔的故事轰动一时,他的书《康-提基号》销量超过2000万册。
对于波利尼西亚人和认真研究波利尼西亚的学者来说,海尔达尔的理论否认了该文化最伟大的成就,这是最大的侮辱。但它激发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举措。首先,它迫使考古学家进行挖掘,寻找并找到能让他们追踪波利尼西亚散居史的具体证据。其次,它促使夏威夷人出海航行。成立于1973年的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于1975年3月8日启动了Hokule’a号。最初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实验开始的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成为一个重新夺回历史和收回被盗遗产的使命。
对考古学家来说,挑战一直是缺乏可用于建立年代学的实物遗存。波利尼西亚人在许多方面技术精湛,但在欧洲人接触时并不使用陶器。1952年在珊瑚海的新喀里多尼亚取得了第一个突破。在那里,在一个名为拉皮塔的海滩附近的偏远遗址,考古学家确实发现了陶器——极具特色的印戳陶瓷,与三十年前在汤加发现的陶片完全相同,而汤加是位于东面2400公里的岛屿。随后在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斐济和所罗门群岛的发现,无疑证实了一个失落文明的存在,这是一个古代文化圈,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从美拉尼西亚向东扩散到太平洋。在史前史的伟大传奇中,一个被我们称为拉皮塔的民族——以新喀里多尼亚的原始遗址命名——离开了他们在新几内亚森林中的原始家园,出发去定居一个世界。在五个世纪内,也许二十代人的时间里,他们逆着盛行风航行,跨越3200公里的水域,不仅到达了斐济,还越过斐济到达萨摩亚和汤加。他们在基督诞生前十个世纪完成了这一旅程。
然后,出于至今未知的原因,这一迁移运动停歇了近一千年。陶瓷传统失传了,但语法和句法、雕刻石头或装饰身体的意义、祖先的力量和风的神圣起源并未失传。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开始,新一波的探索开始了,这次是由现代波利尼西亚人的直系祖先所激发。从萨摩亚和汤加他们向东航行,到达库克群岛、塔希提和马克萨斯群岛,距离约4000公里。然后,在又一个世纪的间歇之后,新的发现出现了,首先是拉帕努伊或复活节岛,然后是夏威夷,后者在公元400年被定居。波利尼西亚侨散的最后伟大阶段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展开,航海者向南向西探索,约在公元1000年在奥特亚罗瓦,即后来的新西兰登陆。在哥伦布之前五个世纪,波利尼西亚人在仅仅八十代人的时间里定居了太平洋几乎每一个岛群,建立了一个涵盖地球表面约2500万平方公里的单一文化生活圈。
设想一下这些旅程意味着什么。航海者乘坐开放式双体船,全部用珊瑚、石头和人骨制成的工具建造。他们的帆由露兜树编织,船板用椰子纤维搓成的绳索缝合;裂缝用面包果汁液和树脂密封。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白天是阳光,夜晚是冷风,饥饿和干渴是永恒的伙伴,这些人跨越数千公里的海洋,发现了数百个新陆地,有些如小大陆般大小,其他的仅仅是直径不到一公里的岛屿环礁,没有比椰子树更高的地标。
虽然无疑存在渔民被吹到海上或在近海追逐远洋鱼群时被风困住的情况,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这些航行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发现之旅。但他们为什么要去?为什么有人要冒生命危险离开像塔希提或拉罗汤加这样的地方前往虚无?声望、好奇心、冒险精神肯定发挥了作用。向着朝阳航行,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这是一种带来极大勇气的行为,为氏族带来巨大荣誉。口述传统表明,这些远征中可能有一半以灾难告终。但由于失败意味着死亡,留下的人们有既得利益去想象成功,在他们的梦想中,他们设想新的陆地从海中升起迎接他们离去的亲属,这些男男女女通过他们的行为本身获得了神的地位。
如在任何文化中一样,也有更世俗的动机。波利尼西亚的继承基于长子继承制,社会结构严格等级化。对于次子或三子,或低贱家庭或氏族的后代来说,获得财富和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到一个新世界。生态需求和危机,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也推动了发现。拉帕努伊或复活节岛的花粉记录表明,直到波利尼西亚人到达之前,该岛被亚热带森林密集覆盖。到欧洲人接触时,景观已被完全改变,许多当地物种灭绝,土壤的大部分财富耗尽。新西兰的不会飞的鸟类在定居后一代内消失。波利尼西亚人完全有能力过度开发自然世界,当他们的人口超过土地承载能力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迁移。这意味着要出海。
无论最终动机如何,古代波利尼西亚人出海了。虽然许多航行确实是探索性的,某些偏远岛屿如拉帕努伊一旦被定居,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孤立,但这些并非全是绝望的单向旅程。相反,所有证据都表明,沿着既定路线的定期长距离贸易纵横交错于海洋。
但是波利尼西亚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们拥有的是口述传统,所有知识都储存在记忆中,代代相传。历史的悲剧之一是早期欧洲人未能努力研究和记录这一非凡的航海知识宝库,更不用说赞美它了,尽管有库克船长等notable exceptions。传统导航者的威望和权威对任何公正的观察者来说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每个社区的文化支柱。导航从根本上定义了波利尼西亚人的身份认同。这些大师被忽视并非仅仅是疏忽,而是征服带来的文化冲突的必然后果。
接触带来了混乱和毁灭。除了导航者之外,波利尼西亚社会的两大支柱是酋长和祭司。酋长的权威基于他控制和分配剩余食物的能力。祭司的权力在于执行tapu(神圣文化规则)的精神能力。当欧洲疾病席卷岛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杀死了马克萨斯群岛高达85%的人口时,人口崩溃摧毁了传统经济,同时也损害了祭司的地位,因为他们无法制裁那些肆无忌惮地违反tapu并且奇迹般地对瘟疫免疫的外国人。在持续接触之后大量涌入海滩的传教士们,将人民自身的不幸归咎于他们,甚至将他们的宗教信仰贬为粗糙的偶像崇拜。在这样的氛围下,欧洲人确实很难承认波利尼西亚人拥有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他们自己水手的航海技能,特别是考虑到航海技术,尤其是在英国,是国家的骄傲。但他们确实拥有这样的技能。
Nainoa Thompson在Hokule’a号甲板上告诉我,当我们在一场激烈的雨中离开Kauai,准备绕过Oahu,然后在夜间从Molokai向北驶向公海时,要理解古代波利尼西亚人的天才,你必须从波利尼西亚世界的基本要素开始:风、浪、云、星、日、月、鸟、鱼,以及水本身。将这些与经验观察的原始力量、普遍的人类探索精神结合起来。传统导航者的技能与科学家的技能并无不同;一个人通过直接经验和假设检验来学习,信息来自自然科学的所有分支:天文学、动物行为学、气象学和海洋学。用终生不可能强烈的承诺和纪律来调和这一切,所有这些都将获得在一个地位至关重要的文化中的最高声望回报。换句话说,人类的全部智慧光辉,连同人类欲望和雄心的全部潜能,都被应用于海洋的挑战。
Nainoa三十多年来的老师是Mau Piailug,一位来自密克罗尼西亚加罗林群岛Satawal的导航大师。Mau在一个面积不到1.5平方公里的珊瑚小岛上长大,比纽约中央公园还要小三分之一。他的宇宙就是海洋。他的祖父是导航者,他父亲的父亲也是。一岁时,Mau被选中来继承祖传的教导。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他在婴儿时期被放置在潮汐池中数小时,以便感受和吸收海洋的节奏。八岁时,在他第一次深海航行中,当他因海浪而晕船时,老师的解决方案是用绳子绑住他,拖在独木舟后面,直到恶心消失。十四岁时,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将自己的睾丸绑在船只的索具上,以更仔细地感知独木舟在水中的运动。Mau不仅学会了航行,还学会了理解Big Water的秘密,波浪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据说他仅仅通过在想象中保持对岛屿的想象,就能从海中召唤出岛屿。
在Mau成就的阴影下,Nainoa,一个来自被剥夺权利的贵族家庭的年轻夏威夷人,他的祖母曾因在教会学校说母语而被殴打,找到了希望并渴望伟大。从Mau那里,他学会了关注天气,解读波浪,理解星星的含义——正如他所说,在脑海中绘制通往岛屿的海图。
Nainoa告诉我,盛行的贸易风确实来自东方,但它们并不像Thor Heyerdahl等人设想的那样以简单的方式主导。正如导航者Tupaia曾经向库克船长解释的那样,每年都有风向逆转的时候,西风吹过太平洋。低压槽形成了一条从澳大利亚北部向东延伸的走廊,正是Lapita文明从俾斯麦群岛迁移到太平洋中部的路线。同样,在更北的地方,更靠近夏威夷,风并不总是持续地只从东方吹来。更重要的是,正如Hokule’a号在十多次深海航行中所证明的那样,即使是满载的独木舟,也可以逆风航行。
古代波利尼西亚人,Nainoa补充道,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航海者,不如说是寻路者(wayfinders)。例如,从塔希提岛航行到瓦胡岛时,他们不是直接驶向珍珠港;而是出发去寻找一串岛屿,即夏威夷群岛。此外,太平洋的距离并不像海图上看起来那么令人生畏。除了波利尼西亚三角最远的三个点——拉帕努伊岛、夏威夷和奥特亚罗瓦(新西兰)——从美拉尼西亚穿越波利尼西亚的任何航行都不必穿越超过500公里的开阔水域,至少按直线距离计算是如此。而且陆地比地图显示的要多。在海上,人们可以向任何方向看到大约50公里。以每个陆地为中心画一个半径50公里的圆,海洋突然缩小了,陆地有效”覆盖”的区域增加了。
云层也为寻路者提供线索——它们的形状、颜色、特征以及在天空中的位置。棕色云彩带来强风;高云不带风但雨水充沛。它们的运动揭示了风的强度和方向、天空的稳定性、风暴锋面的不稳定性。有一整套术语体系来描述云彩聚集在岛屿上空或掠过开阔海洋时形成的独特模式。光线本身也可以解读,星星边缘的彩虹色,它们在即将来临的风暴中闪烁和变暗的方式,岛屿上空天空的色调,总是比开阔海面上空更暗。日出和日落时的红色天空表明空气中的湿度。月晕预示着降雨,因为它是由光线穿过充满水汽的云层中的冰晶造成的。月晕内的星星数量预示着风暴的强度;如果少于十颗,就要预期麻烦、大风和暴雨。如果月亮周围出现双重光晕,天气将伴随着大风到来。
其他征象可以在野生动物和海标中找到,而不是陆标。一条在海中懒洋洋游动的棕褐色鲨鱼。一只与鸟群分离的孤鸟。海豚和鼠海豚游向庇护水域预示着风暴,而军舰鸟飞向海洋则预示着平静。像信天翁这样的远洋鸟类不会指向任何方向,但其他如海燕和燕鸥从巢穴出发有固定的飞行距离,每晚返回陆地,日落时从海浪中升起,它们回家的飞行路径如罗盘方位一样精确。看到白燕鸥表明陆地在200公里范围内;棕燕鸥的活动范围可达65公里,鲣鸟很少超过40公里。磷光现象和海中植物碎屑,水的盐度、味道和温度,剑鱼游泳的方式,所有这些在航海者的感官中都变得具有启示意义。
所有这一切都说得通,直到我们绕过摩洛凯岛的背面,在夜晚的黑暗中向北航行,迎面驶入一场远方的风暴。正如Nainoa告诉我的,知道要寻找什么,这些线索、征象和指示是一回事;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在当下面对大海不断变化的力量和现实则是另一回事。
天空仍然晴朗,海洋漆黑,苍穹被无数星星的寂静所主宰。Hokule’a号在涌浪中颠簸前行,涌浪虽然适中,但仍然强劲,足以使甲板起伏,至少在我看来,完全看不到地平线。船员们分两小时一班轮换,每个人都要轮流掌舵,这不是舵而是一根长长的操舵桨,需要三个人来操作。被夜幕包围,独木舟本身成为了以天空为罗盘的指针。我们身后坐着航海者,一位名叫Ka’iulani的年轻女子,Nainoa的弟子。在整个航程中,她每天要保持清醒二十二小时,只有在大脑需要休息时才会短暂入睡。
Ka’iulani,像Nainoa和所有经验丰富的船员一样,能够命名并跟踪夜空中大约220颗星星。她知道并能追踪所有星座,天蝎座和南十字座、猎户座、昴宿星团和北极星。但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些低垂在天空中的星星,那些刚刚升起或即将落下的星星。Nainoa解释道:随着地球自转,每颗星星都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在天空中划出一条弧线,然后在西方方位落下。这两个地平线上的点,特定星星在东方升起和在西方落下的位置,全年保持不变,尽管星星出现的时间每晚会变化四分钟。因此,只要能够记住所有星星及其独特位置、每颗星在特定夜晚出现的时间,以及它们突破地平线或沉入地平线下时的方位,就可以想象出一个360度的罗盘,夏威夷人在概念上将其分为三十二个星宫,每个都是地平线上以天体命名的一段。任何一颗星星都只在一段时间内可靠,因为当它在天空中划弧时,其方位会发生变化。但到那时会有另一颗星星突破地平线,同样在航海者已知的方位上。在海上度过的一夜——在热带地区大约十二小时——十颗这样的导航星就足以维持航向。为了操舵,掌舵的船员在航海者的指导下,利用独木舟本身,调整船只位置,使特定的星星或天体保持在特定框架内,例如,在桅杆顶部与支撑它的索具之间的夹角内。任何一致的参考点都可以。
随着黎明的到来,太阳升起,这对导航者来说总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刻。这是测量海洋和天空、研究风向并观察其对波浪影响的时机。毛,奈诺阿的老师,仅仅为了识别太阳路径造成的不同宽度和颜色就有数十个名称,当阳光和阴影在水面上升起并移动时。所有这些都告诉他即将到来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Hokule’a的船尾是方形的,这使得导航者能够在日落和破晓时轻松地确定东西方向。船只两侧的栏杆上刻有八个标记,每个标记都与船尾的一个点配对,提供前后两个方向的方位——总共三十二个方位,对应星罗盘的三十二个方向宫位。白天,导航者在概念上将前后的地平线各分为十六部分,以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为基本方位点。因此,白天他或她复制了夜晚的星罗盘。这个隐喻是Hokule’a从不移动。它只是等待,作为世界的轴心,当岛屿从海中升起来迎接她时。
除了太阳和星星,还有海洋本身。当云层或雾气遮蔽地平线时,导航者必须通过水的感觉来定向船只,区分由当地天气系统产生的波浪和由远在地平线之外的气压系统产生的涌浪。而这些涌浪又必须与流经太平洋的深海洋流区分开来,这些洋流可以像陆地探险者跟随河流到河口一样容易地跟随。像毛这样的专业导航者,独自坐在独木舟船体的黑暗中,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感知并区分多达五种不同的涌浪穿过船只。当地的波浪活动是混乱和破坏性的。但远处的涌浪是一致的,深沉而共鸣的脉冲,从一个星宫跨越海洋到180度外的另一个星宫,因此可以用作在时间和空间中定向船只的又一种手段。如果独木舟在半夜改变航向,导航者会知道,仅仅通过波浪俯仰和摇摆的变化。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导航者从海中找出岛屿的能力。像毛这样真正伟大的导航者可以仅仅通过观察波浪在独木舟船体上的反射来识别可见地平线之外远处环礁或岛屿的存在,他们完全知道太平洋中的每个岛屿群都有其独特的折射模式,可以像法医科学家读指纹一样轻易地读取。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凡的,这些个别技能和直觉中的每一个都是某种才华的标志。但当我们孤立、解构甚至庆祝这些特定的智力和观察天赋时,我们面临着错失全部要点的风险,因为波利尼西亚导航的天才不在于特殊,而在于整体,在于所有这些信息点在寻路者心中汇聚的方式。例如,用简单计算测量Hokule’a的速度是一回事:一点泡沫或漂浮物,或者仅仅是一个气泡,经过独木舟横梁之间已知长度所需的时间。三秒钟,速度将是8.5节;十五秒钟,船只缓慢行进,仅为1.5节。
但持续进行这样的计算,日夜不停,同时还要测量破晓时分的星星、风速和方向的变化、穿过独木舟的涌浪、云层和波浪,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导航的科学和艺术是整体性的。导航者必须处理无尽的数据流、从观察中得出的直觉和洞察,以及风、浪、云、星、日、月、鸟类飞行、海带床、浅礁上磷光的动态节奏和相互作用——简言之,天气和海洋不断变化的世界。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整个寻路科学都基于推算定位(dead reckoning)。你只有通过精确知道你曾在哪里以及如何到达你现在的位置才能知道你在哪里。任何时候的位置都完全基于自离开最后一个已知点以来行进的距离和方向来确定。“你不是抬头看星星就知道你在哪里,”奈诺阿告诉我,“你需要通过记住你从哪里航行来知道你来自何处。”
在经度问题通过计时器的发明得到解决之前,正是由于无法在长途航行中跟踪速度、洋流和方位的每一次变化,使得欧洲水手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但这正是波利尼西亚人设法做到的,而且完全没有文字的帮助。没有航海日志、笔记本或海图,没有测速仪、手表或指南针。在深海航行过程中获得的每一点数据——风、洋流、速度、方向、距离、时间——包括其获得的顺序,都必须储存在一个人,即导航者的记忆中。南北纬度总是可以从星星确定,但经度不行。如果导航者失去与参考航线的位置关系,船只就会迷失。这就是为什么卡乌拉尼(Ka’iulani),像所有寻路者一样,在我们短暂旅程中不睡觉的原因。导航者不睡觉。他们保持僧侣般的状态,不受船员干扰,没有世俗任务要执行,独自坐在船尾的特殊栖息处,用心灵追踪。
“如果你能读懂海洋,”毛曾经告诉奈诺阿,“如果你能在心中看到岛屿,你永远不会迷失。”
1976年,在其首次深海航行中,Hokule’a号在毛的指导下从夏威夷航行4400公里到达塔希提,在那里出乎意料地受到了超过16000人的庞大欢呼人群的欢迎。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殖民地管理者就正式禁止了传统文化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包括岛屿间的长距离海洋贸易。Hokule’a号让一切重新焕发生机,仿佛风本身就是穿越时间而来的低语。
1999年,在横跨太平洋从马克萨斯群岛到新西兰之后,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开始了其最雄心勃勃的航程。在奈诺亚担任导航员的情况下,Hokule’a号将尝试从海中找到拉帕努伊岛。这是一次极其雄心勃勃的远征。从夏威夷到复活节岛的距离大约是10000公里,但这次航程需要穿越赤道无风带,并逆风航行2300公里,这实际上将总航行距离几乎翻倍至近20000公里。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一个直径23公里的岛屿上登陆,在罗盘上不到一度——如果船上真的有罗盘的话。食物和水的配给减半以减轻负载。在干船坞中,船只减重4000磅。船员是Hokule’a号有史以来最少的。航线经由马克萨斯群岛到皮特凯恩岛。从那里他们将向南航行,借助西风,然后向东向北航行,直到距离目标的距离大约相当于夏威夷群岛的长度。然后他们将寻找这个岛屿,以网格方式来回航行,小心地在向西的顺风航行中不要越过目标,否则会被风力推向南美洲。
在接近目标的某个时刻,奈诺亚在恍惚中惊醒,意识到由于阴云密布和海雾,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失去了海上生存所必需的思维和记忆的连续性。他向船员掩饰了自己的恐惧,绝望中想起了毛的话。你能在心中看到岛屿的形象吗?他变得平静,意识到他已经找到了岛屿。那就是Hokule’a号,他在这艘神圣独木舟上拥有所需的一切。突然,天空变亮,一束温暖的光线照在他的肩膀上。云层散开,他沿着那束光线直接到达了拉帕努伊岛。
我发现与奈诺亚和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的船员一起在Hokule’a号上航行是一次非凡的体验。尽管毛作为导师和向导对他很重要,但奈诺亚·汤普森已经成为整整一代年轻波利尼西亚人的偶像,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文化人物,在夏威夷受到的公众敬仰超过任何其他人。在各个岛屿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只要Hokule’a号继续航行,导航者的文化就会延续下去。奈诺亚的整个人生使命就是确保这种情况发生。他称Hokule’a号既是神圣的独木舟,也是祖先的宇宙飞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词语选择。确实,如果你把所有让我们能够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天才都应用于对海洋的理解,你得到的就是波利尼西亚。
我被波利尼西亚的故事所吸引,因为它揭示了至今仍激励和困扰我们的问题和误解:真正探索所需要的纯粹勇气,人类适应的brilliance(智慧),征服和殖民主义的黑暗影响。它也提醒我们,总是需要对学术orthodoxy(正统观念)的顽固把持持怀疑态度。知识很少完全脱离权力,而解释往往是便利的表达。
人类学,正如我们在第一次讲座中看到的,产生于一种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十九世纪的学者如路易斯·亨利·摩根和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设想为线性进步阶段,他们认为这种进步从野蛮主义到蒙昧主义再到文明。在他们的计算中,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特定的技术革新相关。火、陶瓷和弓箭标志着野蛮人。随着动物驯化、农业兴起和金属加工的发明,我们进入了蒙昧人的水平。识字意味着文明。人们认为每个社会都以相同的顺序经历相同的阶段。因此,一个民族的技术sophistication(复杂程度)将他们置于通向演化成功的阶梯上的特定台阶。波利尼西亚人和英国人可能是同时代的,但缺乏枪支和大炮意味着前者处于其演化的较早阶段,而库克船长的船员代表着后来更先进的阶段。
这种透明简单且带有偏见的人类历史诠释,尽管早已被人类学家摒弃,认为它是十九世纪的智识产物,就像那些认为地球只有6000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时代牧师的信念一样与当今时代无关,但这种观点却顽强地持续存在,甚至在当代学者中也是如此。最近一本加拿大著作《剥下原住民产业的外衣:原住民文化保护背后的欺骗》嘲笑了这样一个观念:美洲原住民在首次与欧洲人接触时有任何值得向世界提供的东西。“历史上从未有过,”作者写道,“两个民族接触时的文化差距如此之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益地补充道,用一句话指代数千万说着可能多达三千种语言的人们,“[原住民]愚蠢或低劣。我们都经历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阶段。”这样的观点竟能由一位大学教授表达出来,然后被国家媒体抓住作为今天第一民族人民抱负是骗局的证据,这是令人不安的。
美洲给了欧洲烟草、土豆和西红柿、玉米、花生、巧克力、辣椒、南瓜、菠萝和红薯。从新世界来的还有治疗疟疾的奎宁、从亚马逊箭毒中提取的肌肉松弛剂d-筒箭毒碱,以及从印加人称为”神圣不朽之叶”的植物中提取的可卡因。这三种药物深刻影响了西方医学;仅金鸡纳树皮这一奎宁来源就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欧洲向美洲提供了小麦、大麦、燕麦、山羊、牛、非洲奴隶制和钢铁,以及斑疹伤寒、疟疾、麻疹、流感、天花和瘟疫。百分之九十的美洲印第安人在接触后一两代人内死亡。
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令早期西班牙人眼花缭乱,印加的黄金之城库斯科也是如此。据所有当代记录,西班牙没有任何地方能与这两个首都相比。印加帝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保证了免于匮乏和饥饿的自由。沿着安第斯山脊分布的仓库建筑群储备着数十万蒲式耳的藜麦、玉米、lisas、oca、añu,以及大量的chuño——世界上第一种冷冻干燥食品,由前哥伦布时期南美文明驯化的3000种土豆品种中的任何一种制成。
相比之下,征服四个世纪后,伦敦是欧洲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城市。但城市一边的死亡率是另一边的两倍。五分之一的儿童死于出生。据英国军队记录,穷人的孩子平均比富人的后代矮6英寸,轻11磅。杰克·伦敦在描述1901年这个伟大首都的城市生活时——正值其声望和技术优势的顶峰——写到穷人争抢医院垃圾堆,废料堆得很高,“在一个巨大的盘子上形成难以形容的混乱——面包片、油脂和肥猪肉块、烤肉外皮烧焦的皮、骨头,简而言之,所有来自患有各种疾病的病人手指和嘴巴的剩菜。男人们将手伸进这堆混乱中,挖掘、扒拉、翻找、检查、拒绝和争抢食物。这并不美观。猪都做不出更糟的事情。但这些可怜的家伙饥肠辘辘。”
在人类学早期历史中,有一位学者认识到了那些从未进行过田野工作、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念明显因先入之见而扭曲的人所炮制的宏大文化理论的不足之处。弗兰茨·博厄斯是一位物理学家,在爱因斯坦之前一代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博士研究涉及水的光学性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的研究受到感知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开始令他着迷。以十九世纪最优秀学者的博学方式,一个学术领域的探究引向了另一个领域。认知的本质是什么?谁决定什么应该被认知?博厄斯开始对看似随机的信念和信念如何汇聚成这个叫做”文化”的东西产生兴趣,他是第一个推广这个术语作为组织原则、作为有用的知识出发点的人。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他感觉到每个独特的社会共同体,每个以语言或适应倾向区别的人群集合,都是人类遗产及其前景的独特面向。
博厄斯成为现代文化人类学之父,是第一位试图以真正开放和中立的方式探索人类社会认知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不同社会的成员是如何被塑造来观察和阐释世界的学者。他先在巴芬岛的因纽特人中工作,后来在加拿大西北海岸进行研究,他坚持要求学生学习并用当地语言进行研究,并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他们所研究人群的日常生活中。他认为,应该尽一切努力去理解他者的视角,学习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理解他们思维的本质。按照定义,这需要有意愿从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束缚中退出来。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在物理学学科中的独特性一样。博厄斯提出的一切都与正统观念相悖。这是对欧洲思维的冲击,自那时起,人类学家定期被指责拥抱极端相对主义,仿佛每种人类行为都必须被接受,仅仅因为它存在。事实上,没有严肃的人类学家主张消除判断。人类学只是要求暂停判断,这样我们作为人类在道德上有义务做出的判断才能是有根据的判断。
对弗朗茨·博厄斯来说,顿悟的时刻出现在1883年冬天,在他第一次前往巴芬岛进行民族志旅行期间。在一场暴风雪中,气温降至零下46摄氏度,他的队伍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他们乘雪橇跋涉了26个小时,博厄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的因纽特同伴和狗。最终他们找到了庇护所,“半冻半饿”。博厄斯很高兴能活下来。第二天早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常问自己,我们良好的社会比’野蛮人’的社会有什么优势,我发现,我越了解他们的习俗,就越觉得我们没有权利看不起他们……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他们的形式和迷信而责备他们,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很荒谬。相对而言,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糟糕得多。”
博厄斯确立了民族志研究的模板,他的榜样激励了那些后来创建现代人类学学科的人。人类学家的目标是”把握土著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实现他的世界愿景”。这些话虽然可能出自博厄斯之口,但实际上是四十年后由伦敦经济学院的贵族波兰人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写的,他将民族志田野工作提升到了另一个承诺层次。在经济学意味着卡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理论的时代,马林诺夫斯基颠覆了一切,挑战了关于财富本质、交换目的和意义的传统观念,同时他揭示了一个当代海洋贸易网络的动态,这个网络如此庞大和复杂,以至于为最终导致太平洋定居的力量提供了线索。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滞留在美拉尼西亚,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度过了两年,这是一个由平坦珊瑚礁和岛屿组成的群岛,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约250公里处。当时的居民大约有1万人,用他的话说,是”快乐、健谈和随和的”,其艺术技能使他们”在文化上处于美拉尼西亚部落的第一等级”。作为一个有天赋的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迅速掌握了他们的语言并开始工作,很快辨别出了这种文化的大致轮廓。
人们生活在村庄里,主要依靠他们的花园,主要作物是山药,山药的种植和收获决定了一年中社会和仪式周期的起伏。血统是母系的。有四个公认的氏族,以鸟类、动物和植物作为相关图腾。岛屿被分为若干政治单位,每个都由一个男性领导者主导。尽管冲突是地方性的,但战争有精确的规则,战斗主要是长矛和盾牌的戏剧性展示。
男女之间的分工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奇怪地公平。女性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通过她们的劳动控制经济的要素,并实施她们自己的魔法形式,这与诱惑无关,尽管性对马林诺夫斯基来说成了某种痴迷。作为自己世界不可避免的产物,他被年轻特罗布里恩少女享有的自由所震惊。在结婚前,似乎什么都可以。一旦正式结婚,忠贞就被高度珍视,通奸会受到严厉制裁。马林诺夫斯基在他根据在岛上的时光写的两本书中的一本里对此进行了长篇思考。然而,他的第二本书才是我们关注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因为这讲述了海洋的故事。
马林诺夫斯基乘船到达特罗布里恩群岛,经历了汹涌的洋流和开阔海洋的航行,这足以让任何来自他出生地——波兰内陆城市克拉科夫的孩子印象深刻。他想知道人们如何能够跨越这样的障碍维持社会联系。虽然特罗布里恩岛民几乎完全依靠陆地谋生,但他们的贸易却通过水路进行。然而,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从表面上看,他们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合理解释他为到达那里而忍受的单程航行的风险。他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实用性无关,这是一个奇特的交换系统,其中没有明显价值或值钱的东西在巨大的风险下移动,却承诺着巨大的声望。他发现,特罗布里恩群岛只是一个贸易网络中的众多据点之一,这个网络连接着海洋数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数十个社区,这些小小的聚集人群紧贴着珊瑚礁,分布在沉没山脉的遗迹上。
这个被称为库拉环(Kula ring)的系统是一个基于两种物品仪式性交换的平衡互惠体系:一种是由红色海菊蛤贝壳雕刻成圆盘制成的项链,称为soulava;另一种是白色锥贝制成的臂环,称为mwali。这些严格来说是象征性物品,没有内在或实用价值。然而,至少五百年来,男人们一直准备冒着生命危险,携带这些珠宝穿越数千公里的开阔海域。项链多年来按顺时针方向移动,而臂环则反向流动,总是按逆时针方向移动。参与贸易的每个人至少有两个伙伴,这些关系就像婚姻一样,旨在持续终生,甚至由后代继承。航行者会向一个伙伴赠送项链以换取等值的臂环,向另一个伙伴传递臂环并获得项链作为回报。每个联系人在另一个岛屿上都有他的第二个伙伴,因此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分配链。交换不是一次性发生的。一旦拥有了一件高价值的物品,人们期望在一段时间内享受它所带来的声望,同时制定最终传递它的计划。当一个物品在库拉环中移动时,可能需要长达二十年才能完成一轮,然后继续循环,它的价值随着每次航行、每个关于艰辛和奇迹的故事、巫术和风的故事,以及所有经过它的伟人的名字而增长。因此,这些神圣的物品在不断运动中,环绕着分散的岛屿形成社会和魔法力量的环链。
马林诺夫斯基理解并撰写了库拉环的功能目的。它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建立了跨越巨大距离的关系,促进了实用物品、颜料和染料、石斧、黑曜石、陶瓷、抛光仪式石、编织品和某些食物的最终双向流动。库拉还为展示声望和地位提供了背景,世袭酋长的权威正是基于此。他们的名字与最有价值的臂环和项链相关联,组织和领导航行的责任落在他们身上。准备工作既严格又昂贵。来自相距甚远的村庄的男人必须协调配合。必须种植花园,仅仅是为了种植在航行准备期间要消耗的食物。有禁忌要执行,仪式魔法要进行,盛宴要庆祝,旅行用品要获取和储存。必须建造独木舟船队,用露兜树叶编织新帆,打磨和涂装舷外支架,雕刻桨叶,以及对华丽的船首进行仪式清洁和赋能,以抵御所有邪恶——巨大的海洋生物、活石头、居住在深海中吞噬遇难者的女巫。几个月过去了,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兴奋感日益增长。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他著作标题中如此优雅地概括的那样,航行者真的就像阿尔戈英雄一样驶向未知,寻求荣誉和荣耀,不确定是否还能再次看到家乡和家人,被冒险的刺激和开阔水域的诱惑驱动。“在当地独木舟中航行总是美丽的,”马林诺夫斯基写信给他的妻子埃尔西,“它给你一种在筏子上的印象,完全在水面上,仿佛奇迹般地漂浮着。”
几年前,我有幸驶过特罗布里恩群岛,这次旅程始于斐济,经过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然后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水域。最终我们环绕了库拉环的大部分,从东向西经过伍德拉克岛到基塔瓦和基里维纳——马林诺夫斯基的基地,然后向南到德博伊恩群岛,像soulava项链一样按逆时针方向移动,最终前往莫尔兹比港。与马林诺夫斯基不同,我们乘坐一艘探险船舒适地旅行,配备了一小队橡皮艇,让我们能够在几乎任何海岸登陆,天气和洋流允许的情况下。我记忆最深的地方是劳克林群岛中的博达卢纳岛,这是我们与库拉环的第一个接触点。我们从朝阳方向穿越数百公里宽的开阔海洋——所罗门海而来。对特罗布里恩岛民来说,博达卢纳是他们世界的最极端点,是库拉环最东端珊瑚环礁上的一个小岛。
Bodaluna是我去过的最偏远和孤立的地方,一片位于珊瑚礁边缘的沙地,海拔最高点不超过一米,除了几棵椰子树和鸡蛋花树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御台风的侵袭。岛上的人们,大约二十户人家,靠着用珊瑚碎屑制成土壤的小花园,以及珊瑚礁和远海维持生计;巨大的蛤壳散落在沙滩上,渔网沿着海岸晾晒。他们的房屋结构简单,主要是椰子茅草覆盖在棕榈木骨架上。孩子们有着古铜色的皮肤,所有人都戴着白色和红色的贝壳项链,头发上插着白色芳香的花朵。
沿着海岸,我遇到了一艘Kula独木舟,被拖上沙滩,用椰子叶遮挡风雨。它似乎已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精雕细琢的挡浪板,或称lagim,围绕着船体末端,以及它所依托的装饰性破浪器或tabuya,都被阳光晒成了灰白色,只剩下白色油漆的碎片。我用手指抚摸着浅浅的雕刻,所有那些象征着魔法智慧和精神飞翔的符号都因暴露而褪色了。这确实是一艘masawa独木舟,专门为Kula而建造,但我对它的小巧感到惊讶,宽度不到2米,长度勉强超过Hokule’a甲板的宽度。船体用树脂填缝,用椰子壳炭和香蕉汁制成的油漆涂成黑色,短木桅杆用纤维绳索固定,它躺在沙滩上就像在水中一样笨拙,略微倾斜,这样稳定的支架可能只是掠过海面。这种设计并不令人信心满满。一旦下水,它无法掉头,更不用说逆风航行了。它是为了点对点航行而建造的,顺风航行,就像箭矢沿着单一轨迹飞行。Kula意味着,如果说什么的话,就是承诺。
东方正在酝酿一场风暴,穿过云层的光线使大片海域变暗,而西方的太阳在沙滩上投下阴影,照亮了近海的绿松石色海水。在珊瑚礁上,年轻的男孩们意识到即将来临的风暴,正划船返回陆地。看着他们,我试图想象坐在这个小岛上,突然从地平线上出现一支Kula独木舟船队会是什么样子,一次多达八十艘,全都涂着鲜艳的颜色,装饰着海贝、羽毛和花环。在拥挤的独木舟上,大约五百名男子会准备数小时,用椰子油涂抹自己,在头发上装饰红色木槿花,进行私人仪式并施展旨在诱使岛民交出Kula珍宝的法术,从而确保远征的成功。在沙滩上,整个岛屿的人口,假装敌意,会聚集等待来访船队首领的召唤。仍在近海,他会大声呼唤他们慷慨欢迎,确保收到的礼物与那些经过如此遥远、冒着如此风险和代价携带来的礼物相等。来自海滩的海螺号角合奏随后会确认这一义务,Bodaluna的每位重要人物会走进浪花中献上礼物。只有在交换完成后,访客才会下船上岸。
他们会停留多久取决于风向。时间意义不大。财富的定义不是拥有,而是通过慷慨给予而获得的声望和地位,从而确保一个社交网络,一种文化的人力资本,一个仪式债务和义务的宝库,这将为一个人的氏族和家庭永远产生利益。
当我们离开岛屿,在珊瑚中人工开凿的狭窄水道中航行时,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我所欣赏的那艘Kula独木舟属于一群被风困住超过四个月的男子,他们在等待航行回家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融入了这个小珊瑚环礁的生活圈子。如果我们的船期望再次经过这里,他们问我们的一名船员,也许我们可以载他们一程。他们向东走,我们向西走。事实上,我们的船确实期望返回,但不会很快。六个月就可以,这是他们的回应。虽然我不认为这正是Thor Heyerdahl心中所想的,但这或许解释了允许人类定居那片浩瀚无垠海洋的勇气和耐心。
阿纳康达之民
“在西方,时间如金钱。你储存它,失去它,浪费它,或者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在Barasana语言中没有时间这个词。” — Stephen Hugh-Jones
让我们以西班牙征服时期阴暗岁月中的一个故事来开始这第三次马西讲座。1541年2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同父异母兄弟、印加征服者冈萨洛·皮萨罗开始了一场穿越安第斯山脉寻找黄金国和传说中的卡内拉(肉桂和黄金之地)的旅程。他带着220名士兵、4000名当地搬运工和2000头猪作为食物离开基多,远征队翻越了科迪勒拉山脉的高峰,开始在云雾森林中缠绕的藤蔓和矮树间进行漫长而缓慢的下降。当他们到达热带低地时,那里的河岸在夜晚闪烁着黑凯门鳄的光芒,猪和马早已被吃掉,大多数印第安奴隶已经死亡,还有140名西班牙人也丧生了。幸存的人们只能炖煮皮革和野草,四处搜寻让其中几人因毒素而精神错乱的根茎和浆果。绝望之中,冈萨洛派遣他的副指挥官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带着49名士兵沿着高原丛林支流寻找给养和拯救。这群人中有一位身穿白袍的多明尼加修士加斯帕尔·德·卡瓦哈尔,他写下了后续旅程的惊人记述。
到达纳波河(这只是流入亚马逊河的1100条主要河流之一)后,奥雷利亚纳率领的士兵们叛变了,在痛苦中拒绝按照原定命令返回上游。水流太湍急,而且无论如何也没有找到食物。奥雷利亚纳以征服者们闻名的法律形式主义,正式辞去了他的职务,以加斯帕尔·德·卡瓦哈尔为证人,这样他就可以通过欢呼接受在这群疲惫不堪的幸存者中的新指挥权。抛弃冈萨洛·皮萨罗听天由命,奥雷利亚纳和他的队伍在1541年圣诞节后的一天出发进入未知之地,乘坐用丛林树木和从死马蹄子上搜集来的铁钉匆忙制作的小船沿着湍急的纳波河顺流而下。
在太阳的折磨下,夜晚被吼猴的咆哮、青蛙和蝉令人产生幻觉的低沉嗡嗡声以及美洲豹意外的吠叫声所困扰,几天后他们到达了纳波河与乌卡亚利河的汇合处,后者是亚马逊河上游在秘鲁的名称。在那里,令他们恐惧的是,他们发现河岸两旁排列着印第安人的定居点,每个都通过传令鼓声与下一个相连,这保证了在河流的每个弯道都会遭到敌对的接待。三名西班牙人死亡,成为飞行死神的目标——涂有箭毒的飞镖从森林中无声射出。加斯帕尔·德·卡瓦哈尔本人被一支箭射瞎了一只眼睛,幸运的是这支箭没有毒,这对历史来说是件好事。他的日记记录了被疾病折磨的人们的痛苦,他们昏昏欲睡的身体被寄生虫穿透,肠胃因缺乏食物而痉挛。这确实是残酷的折磨,因为每过一公里,当地村庄的富裕和繁荣只会增加,田野的丰饶、居民的美貌和数量以及高等文化的明显精细程度也在增加。九天后经过几百公里,西班牙人进入了奥马瓜人的土地,惊讶地发现沿岸有一系列连续的村庄绵延约320公里,据卡瓦哈尔报告,每个村庄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弩之遥。一个社区延伸了五里格,大约25公里,是一个茅草屋顶房屋的集中地。
六个月后,奥雷利亚纳的队伍经过了里约内格罗的汇合处,这是一条比密西西比河大四倍的支流,如果它存在于任何其他大陆上,它将是地球上第二大河流。森林、河流和天空的规模完全震撼了他们的感官。在里约纳蒙达河岸上,再往下游两天的地方,他们遇到了自称是凶猛女战士部落附庸的印第安人,这些女战士是居住在遥远源头、盐水湖边石头村庄中的女性文明的边缘居民。在那里她们骑骆驼,穿着最精美的编织布料,在用金刚鹦鹉羽毛和鹦鹉羽毛装饰的神庙里崇拜太阳神。为了繁殖,她们仅为了育种目的而俘虏男性;所有男性后代都被立即杀死。据卡瓦哈尔说,两周后,远征队进入了亚马逊女战士的土地,实际遇到并与由女性队长率领的印第安人中队作战——裸体女性,高大而白皙,长长的辫发盘绕在头上。每个人都有十个男人的力量,只有在几个被杀死后,西班牙人的双桅船被箭射得千疮百孔才逃脱。
西班牙人越往下游漂流,定居点就越精细。在里约塔帕霍斯河口,靠近现代巴西圣塔伦市,远征队遇到了由200艘战争独木舟组成的舰队,每艘载着30名男子,全副武装,穿着华丽的羽毛斗篷,戴着像太阳一样闪耀的王冠。数千名居民警惕地站在岸边。一百公里内的河岸密集分布着房屋和花园,远离岸边的地方有,如卡瓦哈尔所写,“非常大的城市”的迹象。
最终,在1542年8月24日,在纳波河出发八个月后,离开基多凉爽山风一年半后,奥雷利亚纳赤裸的队伍因饥饿而虚弱得无法划船,到达了救赎和大海,他们仍然被带给他们的河流的奇迹所震撼。在三角洲有欧洲国家大小的岛屿。河岸,就其本身而言,相距超过300公里。远征队蹒跚地出海,在距离海岸数公里、看不到陆地的地方,海水才变得太咸而无法饮用。
返回秘鲁后,加斯帕·德·卡瓦哈尔完成了他的日记,这是一个非凡的冒险和发现传奇,但几乎立即被讥笑为荒谬之谈,甚至被他的神职同僚斥为pura mentiras,一派谎言。他的问题在于关于女战士的奇幻故事,在批评者看来,这显然是杜撰的,因为它与希腊神话和希罗多德的记述如此相似。Amazon这个词源自”a-madzon”,意思是”无乳房”,长期以来指的是生活在地中海已知世界之外的传说中的女战士民族,据说她们会切掉右乳以便在战斗中使用弓箭。她们作为战士的名声如此响亮,以至于赫拉克勒斯在第九项劳役中被要求夺取她们女王的腰带。在新世界的野蛮腹地发现这样的女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卡瓦哈尔并不是第一个声称遇到过她们的人,尽管是在一个新的地点。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寻找印度群岛的证据时,回想起马可·波罗在中国海发现的女人岛,向伊莎贝拉女王描述了一个女人岛,那里的女人没有男人陪伴生活,穿着铜制盔甲,与食人族为侣。阿美利哥·韦斯普奇在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岛发现了食人的女人。科尔特斯派遣他的表弟弗朗西斯科沿墨西哥海岸北上,调查关于一片由神话中的黑人女王卡利菲亚统治的女人之地的报告——因此有了加利福尼亚这个名字。事实上,就像黄金国和青春之泉一样,女战士之地出现在每个探险者的行程单上。随着时间推移,欧洲神话被美洲印第安人的丰富想象力所修饰,他们从残酷的经验中学会了告诉白人他们想听的一切。因此,女战士的故事以一种新的、栩栩如生的形式反馈回旧世界,这种形式具有真实性的特征,将神话转化为历史。查理五世国王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的缘故,一直被称为Mar Dulce(甜水海或淡水海)的河流有了新名字——Río Amazonas,亚马逊河。但是,像早在1552年就写作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这样的怀疑论者仍然不信服,认为卡瓦哈尔的整个叙述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努力,旨在掩盖奥雷利亚纳背叛指挥官贡萨洛·皮萨罗的事实,而且他的探险既没有发现黄金也没有发现肉桂,也没有为王室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被宫廷流言和阴谋所掩埋,基本上被历史忽视,卡瓦哈尔的《记述》——第一次欧洲人沿世界最大河流顺流而下的记录——直到1895年才得以出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这位修士没有谈到亚马逊女战士,他的非凡日记可能早就因为他确实看到并忠实记录的内容而受到赞誉,这些观察在今天对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如同启示。欧洲人接触时期的亚马逊并不是空旷的森林,而是文明的动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家园。
到我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植物学学生时,丛林——一个早已过时的词——已经成为了伊甸园,但肯定是一个脆弱的伊甸园,正如我在第一篇发表的论文中写到的”生命的聚宝盆”,“远比看起来更加脆弱。事实上,许多生态学家称热带森林为虚假的天堂。问题在于土壤。在许多地区,本质上根本没有土壤。这是一座建立在生物学高度复杂性基础上的城堡,但实际上是建在沙子的基础之上”。这个相当大胆的陈述,以其自己的方式与绿色地狱的概念一样陈词滥调,在我进入研究生院时,已经成为新兴保护生物学运动的咒语。其科学灵感来自苔藓学家、苔藓研究者保罗·理查兹的一项经典研究,他的开创性著作《热带雨林》于1952年首次出版。
正如理查兹指出的,森林有两种主要策略来保存生态系统的营养负荷。在温带地区,随着季节的周期性变化和由此产生的丰富有机碎屑的积累,生物财富存在于土壤本身。相比之下,在热带地区,由于持续的高湿度和年平均温度徘徊在27摄氏度左右,细菌和微生物一旦叶子落到森林地面就会分解植物物质。90%的根尖可能在土壤表面10厘米内找到。重要的营养物质立即被循环到植被中。这个生态系统的财富就是活着的森林,是一个由数千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生物组成的极其复杂的马赛克。
移除这个树冠会引发一连串的破坏反应。温度急剧上升,相对湿度下降,蒸腾作用速率急剧下降,交错在森林树木根部、增强其吸收营养能力的菌根垫干涸死亡。没有了植被的缓冲,暴雨造成侵蚀,导致营养进一步流失和土壤本身的化学变化。“在亚马逊某些被砍伐森林的地区,”我不祥地警告道,“淋滤暴露土壤中氧化铁的沉淀导致了绵延数英里的红土粘土沉积,形成一种岩石般的红土路面,连杂草都不会生长。”
虽然这个模型作为理解热带森林基本动态的方式在根本上是合理的,但当它被广泛应用于像亚马逊这样广阔的地区时,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口号。首先,它暗示盆地具有生态一致性,而50年的实地研究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简化。亚马逊的三分之一是稀树草原。也许一半是高地森林,但不仅在动植物物种方面,而且在地貌和土壤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没有任何简单的方案能够涵盖安大略省七倍大的地理区域。但脆弱性的概念之所以成立有两个原因。首先,它符合环境议程,以及人们对亚马逊森林砍伐速度的合理关切,其中大部分是由巴西南部农业边界的扩张造成的。其次,与这个故事更相关的是,森林是边缘环境的观点符合西方对在亚马逊作为原住民生活意味着什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1743年,法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夏尔·玛丽·德·拉·孔达明率领第一支科学探险队沿河而行。他的民族植物学发现是非凡的。他是第一个确定奎宁为疟疾治疗药物的人,第一个描述橡胶的人,第一个检查箭毒(curare)植物来源的人,也是第一个报告barbasco存在的人——这种鱼毒会产生可生物降解的杀虫剂鱼藤酮(rotenone)。他从印第安人那里了解了所有这些非凡的植物,然而他对森林民族的蔑视却是无以复加的。“在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写道,“必须首先让他们成为人类。”他把印第安人看作儿童,发展停滞,被困在一个他敬畏但最终一无所知的森林中。
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大批进入亚马逊时,幸存的土著文化大多生活在盆地周边的偏远上游地区。河流的主干和其主要支流的下游已经被欧洲人定居了400多年。确实,一个独特的世界已经出现,一个由caboclos组成的河流农民阶层,这些混血男女的整个生存基础都来自土著的先例和适应。但在亚马逊主要洪泛区的原始居民中,只存在沙滩上的阴影,森林中的低语信息。
人类学家,特别是民族志学者,自然被现存的民族所吸引,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印第安人。这些社会中的许多都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东侧,呈一个宽阔的弧形,沿着亚马逊盆地的边缘从南部的玻利维亚延伸到北部的哥伦比亚,然后穿过委内瑞拉南部、奥里诺科河上游和圭亚那地盾的南侧。安第斯山脉是一道可怕的屏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道路从西部穿越。我所认识的许多文化,玻利维亚的Chimane和Mosetene,秘鲁montaña地区的Machiguenga和Campa,厄瓜多尔低地的Cofán、Siona-Secoya和Atshuar,委内瑞拉的Yanomami,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经历持续接触。我在1981年与之生活的Waorani直到1958年才被和平接触,尽管他们的家园距离厄瓜多尔国家首都基多仅150公里,而基多是一个定居了400多年的城市。1957年,五名传教士试图接触Waorani并犯了一个关键错误。他们从空中投下了8×10英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他们做友好姿态的样子,忘记了森林中的人们一生中从未见过任何二维的东西。Waorani从森林地面捡起照片,看着面孔后面试图找到人物。什么也没看到,他们得出结论这些是魔鬼的名片,当传教士到达时,他们立即用长矛将他们刺死。顺便说一下,Waorani不仅刺杀外人,他们认为所有外人都是cowade,或食人族。他们也相互刺杀。在八代人中,54%的死亡率来自部落内部的长矛袭击。
瓦奥拉尼人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非凡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符合许多边缘社会共有的基本模式——这里所说的边缘仅仅是指他们生活在流域的边缘地带。这些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数较少,没有等级制度或密集的专业化分工。他们往往是无首领的,缺乏明显的政治领袖,而最典型的特征可能是他们实行内婚制。他们在自己内部通婚,生活在孤立中,经常与邻居发生公开冲突。当然,他们拥有非凡的天赋。瓦奥拉尼猎人能够在森林中从四十步外闻到动物的尿液并识别物种。通过几代人的经验观察和实验,他们学会了相当熟练地利用植物。从植物中提取的毒素使他们能够捕鱼和狩猎。像死藤水(ayahuasca)这样的致幻剂制剂展现了超越科学理解范围的炼金术天才。在森林中谋生时,他们通过刀耕火种农业找到了一种方法,尽管土壤营养贫乏,仍能种植食物。从森林中开辟的小块土地被点燃烧毁,种植和收获的回报不断递减,大约三年后就被废弃,重新被森林占据。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依赖于人口密度。人口过多会导致田地过多,植被没有时间再生,土地枯竭,环境承载能力达到饱和。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文化情景成了人类学家理解亚马逊土著生活的过滤器。据此暗示,社会只能在危险的生存状态中岌岌可危地生存,始终受到环境及其限制的约束。1971年,史密森学会的知名考古学家贝蒂·梅格斯出版了《亚马逊:虚假天堂中的人与文化》(Amazonia: Man and Culture in a Counterfeit Paradise)一书,该书成为几乎所有南美洲人类学入门课程的必读书目。梅格斯描绘了一个小型狩猎采集社会的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其中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养活超过一千人,这个数字是她任意确定的。她认为,在下游河流的洪泛平原上可能确实出现过更高的人口,正如加斯帕尔·德·卡瓦哈尔曾经报告的那样,但证据模糊不精确,而且沿着河流主干”土著文化模式在被发现后的150年内就完全被摧毁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考古遗迹的保存在亚马逊和在波利尼西亚一样都是个问题。但从1980年代开始,新技术揭示了意想不到的世界。在三角洲的马拉若岛上工作时,考古学家,特别是安娜·罗斯福,发现了一个复杂文化的证据,可能有多达十万人分布在数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持续了至少一千年。在里约内格罗河与亚马逊河汇合处的马瑙斯市附近,大型土制墓冢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提供了证据表明无论是谁占据了这片土地,都利用了大约138种驯化植物,其中大部分是果树和棕榈树。与此同时,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在整个亚马逊地区发现了奇异的现象,大片但孤立的terra preta(黑土)区域,明显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表明人们实际上定居下来,并积极致力于提高土地的农业潜力,用木炭保持养分,用有机废料做堆肥。来自杜兰大学的民族植物学家威廉·巴利认为,亚马逊高地森林多达十分之一的面积,相当于法国大小的区域,可能都是原住民以这种方式培育的。
这些观察促使其他学者质疑关于刀耕火种农业起源和影响的传统假设。当我生活在瓦奥拉尼人中间时,这个民族在接触时仍然使用石器工具,我经常想知道这样的工具怎么可能砍倒热带硬木,而我作为一名植物学家和曾经的伐木工人,用现代斧头都很难砍倒这些树。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并决定进行实验。用石斧砍倒一棵1米粗的树需要115小时,相当于三周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清理半公顷的土地需要相当于153个八小时工作日。根据贝蒂·梅格斯和其他权威的说法,这样的田地只能密集耕作三年就必须废弃。考虑到个人时间的其他需求——狩猎、捕鱼、仪式义务——投入如此多的努力却获得如此少的回报,这将是完全不实用和完全不适应的。人们不会砍伐、焚烧、种植、收获然后迁移,而是有充分的动机定居下来。正如地理学家威廉·德内文所写的那样,“将轮作或刀耕火种描述为印第安人与自然保持永恒平衡的古老做法完全是一个神话。”亚马逊的刀耕火种农业可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是由接触后引入钢铁工具而成为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流域边缘民族的农业技术,这些民族人数较少,土地足够大,能够吸收其几乎荒诞的低效率。但显然,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知道曾经存在于亚马逊主要河段沿岸的密集人口文化生活的基础。
今天的人类学家认识到,我们对这些古老世界的理解长期以来一直被我们对边缘社会的经验所过滤,这些社会在事实上是一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通过这种视角来理解盆地的史前史,就像试图在伦敦被核弹摧毁后从赫布里底群岛的角度重建大英帝国的历史一样。在接触后的一个世纪内,疾病和奴隶制横扫了数百万原住民的生命。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亚马逊有一个地方,这些伟大文明的韵律仍然可以被感受和听到,这就是一个非凡文化复合体的家园,统称为蟒蛇之民(Peoples of the Anaconda)。
1975年,当我第一次前往哥伦比亚西北亚马逊地区时,我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停在了比利亚维森西奥,这是一个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小城市,去拜访一位传奇的博物学家费德里科·梅德姆,他是一位拉脱维亚伯爵,逃离了俄国革命,在热带低地的森林中找到了新生活。他是我大学教授理查德·埃文斯·舒尔特斯的老朋友,这位植物学探险家因1938年在墨西哥发现魔法蘑菇而引发了迷幻运动,后来在亚马逊最偏远的地区连续度过了十二年。我在傍晚时分在他家中找到了梅德姆博士,那是一个杂乱的院落,像是一个老橡胶贸易商的住所。房子有木地板和铁皮屋顶,一个挂着吊床的开放式阳台,墙上装饰着美洲豹和丛林蝰蛇的皮。在他办公室的头顶上,一台吊扇在桌子上投下微弱的阴影,他抚摸着一件工艺品,或者用手指抚摸着一个世纪前手绘的褪色地图。他最珍贵的财产是一条萨满的项链,一根棕榈纤维穿过一块6英寸的石英水晶。他将其描述为太阳父亲的阴茎和结晶的精液,解释说其中有三十种颜色,都是必须在神圣仪式中平衡的不同能量。这条项链也是萨满的房子,是他服用yagé(也被称为死藤水的致幻药水)时去往的地方。一旦进入其中,萨满向外看世界,俯瞰他的人民的领土和神圣的地点——森林、瀑布、山地悬崖和黑水河流——观察着动物的方式。
在梅德姆退下休息后很久,我仍然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读他推荐的一本书《亚马逊宇宙》,这本书是由他的好朋友、哥伦比亚最重要的人类学家赫拉多·雷谢尔-多尔马托夫撰写的,他也是舒尔特斯的密切同事。正是从雷谢尔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河流的重要性。对于沃佩斯(Vaupés)的印第安人来说,河流不仅仅是交通路线,它们是大地的血管,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纽带,是祖先在时间开始时旅行的路径。印第安人的起源神话各有不同,但总是述说着从东方开始的伟大旅程,述说着巨大的蟒蛇从东方沿着牛奶河(Milk River)带来的神圣独木舟。独木舟内是第一批人类,连同三种最重要的植物——古柯、木薯和yagé,这些都是太阳父亲的礼物。蟒蛇的头部有耀眼的光芒,独木舟里按等级秩序坐着神话中的英雄:首领;作为舞者和吟唱者的智慧守护者;战士;萨满;最后,在尾部,是仆人。他们都是兄弟,太阳的孩子。当巨蛇到达世界的中心时,它们躺在大地上,伸展成河流,它们强大的头部形成河口,尾巴蜿蜒通向偏远的源头,皮肤上的涟漪产生了急流和瀑布。
每条河流欢迎一艘不同的独木舟,在每个流域中,五个原型英雄上岸并定居下来,地位低下的仆人前往上游,首领占据河口。因此沃佩斯河流被创造并有了人口,德萨纳(Desana)人在帕普里河(Río Papuri)诞生,巴拉萨纳(Barasana)和塔图约(Tatuyos)人在上皮拉帕拉纳河(Piraparaná),图卡诺(Tucano)人在沃佩斯河,马库纳(Makuna)人在波佩雅卡河(Popeyacá)和下皮拉帕拉纳河,塔尼穆卡(Tanimukas)和莱图阿马(Letuama)人在米里蒂河(Miriti)和阿帕波里斯河(Apaporis)。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中描述的等级制度瓦解了,在每条河流上,那些曾在同一艘神圣独木舟中旅行的后裔开始生活在一起。他们认彼此为家人,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为了确保没有兄弟娶妹妹,他们发明了严格的规则。为了避免乱伦,男人必须选择说不同语言的新娘。
今天,当一个年轻女性结婚时,她搬到她丈夫的长屋。他们的孩子将用父亲的语言抚养,但自然会学会母亲的语言。与此同时,母亲将与孩子们的姑妈——她们父亲兄弟的妻子们——一起工作。但这些女性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因此,在一个定居点中,可能会说多达十几种语言,一个人流利掌握多达五种语言是很常见的。然而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种语言的完整性并没有受到侵蚀。词汇从不混合或简化。语言也不会被那些试图学习它的人违背。要学习,人们在掌握语言之前只听不说。
这种不寻常婚姻规则——人类学家称之为语言外婚制(linguistic exogamy)——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们生活中存在某种紧张关系。由于寻找潜在婚姻伴侣的需求持续存在,而相邻语言群体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文化机制必须确保符合条件的年轻男女定期聚会。因此,如Reichel-Dolmatoff所写,标志着一年中各个季节的聚会和盛大节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神圣的舞蹈、神话的吟诵以及古柯叶和yagé的分享,这些庆典促进了整个社会体系所依赖的互惠和交换精神,同时通过仪式将生者与他们的神话祖先和时间的起源联系起来。
被我所读到的内容所吸引,我安排了第二天早上搭乘军用货机前往Mitú,这是一个没有公路通达的小定居点,坐落在Río Vaupés的一个弯道上,距离Villavicencio三小时航程。飞机没有舱门,我感觉就像坐在皮卡车的后斗里穿越天空。我在Mitú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当地印第安人——主要是Cubeos和Tucanos——一起进行植物学研究,但从未接近他们世界的核心,无论是在精神上、文化上还是地理意义上。森林如此广阔,距离太过遥远,河流黑暗而美得惊人,但被无尽的急流和瀑布所阻隔。
两年后我重返此地,说服一位传教士飞行员将我送到Río Piraparaná上的圣米格尔天主教传教站,这里位于Barasana人的家园,比Mitú更深入森林一小时的路程。这大概是人们在西北亚马逊能设想的最偏远的目的地了。但这也只是一次短暂的访问,语言和礼仪的障碍——我实际上是突然从天而降,许多Barasana人几乎不会说西班牙语——让我对这个地方只有肤浅的了解,以及一种悲哀的感觉: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一种非凡的文化注定要消失。这是当时人类学家的常见哀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我们认为正在消失的世界。
但是,在我最初笨拙地访问西北亚马逊很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986年,新当选的哥伦比亚总统Virgilio Barco Vargas任命人类学家、Reichel-Dolmatoff的门生Martin Von Hildebrand为土著事务主管,并告诉他要为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做些什么。Martin曾在Tanimukas人中生活多年,还在年轻的研究生时代首次划船穿越了整个Río Piraparaná,他所做的远不止”一些事情”。在非凡的五年时间里,他为哥伦比亚亚马逊的印第安人确保了约2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合法土地权利,大约相当于英国的面积,总共建立了162个保留地(Resguardos)——这些被法律确认的土地在1991年被编入该国政治宪法。从未有过民族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在随后的几年里,当哥伦比亚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遭受战争蹂躏时,一层隔离的面纱落在了西北亚马逊上。正如Martin在2006年邀请我与他一起重返Río Piraparaná时所解释的,在这层面纱后面,大地的古老梦想重新诞生了。
在从Mitú起飞的前一晚,Martin和我蜷缩在简陋住所的水泥地板上,服用古柯叶和烟草,Barasana萨满Ricardo Marin在一张大地图上指出了我们即将从空中看到并通过河流和小径访问的神圣地点。Martin和他在Gaia Amazonas基金会的同事们——这是一个与哥伦比亚亚马逊五十多个民族合作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已经将Ricardo所知存在于多维空间中的事物编码成了二维形式。在Barasana语中没有时间这个词,这些神圣地点不是遥远神话事件的纪念物或象征。正如Ricardo所解释的,它们是活生生的地方,永远影响着现在。对他的人民来说,过去就是现在,这些神圣地点至今仍被神话生灵所栖居。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小飞机升入云端,然后像黄蜂一样突破树冠,显得微小而无足轻重。森林延伸到地平线,最初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人类曾经踏足过这片土地。Ricardo坐在我前面,我专注地观察着他凝视这片景象的样子,想要看到他所看到的。那个早上我们飞行了四个小时,环绕了蟒蛇人民的整个世界,从Mitú向东飞越Río Papuri,然后沿着Taraira和分隔哥伦比亚与巴西的古老山脊向南飞行。到达Río Caquetá和Apaporis的汇合处后,我们向西转向,飞越Yuisi和Jirijirimo的巨大急流到达Kananari河口,然后沿着这条河向北穿越比安第斯山脉诞生还要古老的砂岩悬崖。向西我能看到Cerró Campaña在地平线上的遥远轮廓,以及Sierra de Chiribiquete巨大的平顶山脊,这些隆起的高原台地巨大而遥不可及。云朵掠过树冠,有一刻,一道完美的彩虹横跨天空,两端都触及Río Apaporis两侧的森林,河流在彩虹下方如蛇一般流淌,穿过静寂而永恒不变的森林。
我们在当天很晚的时候降落在圣米格尔的土质飞机跑道上,这是我在1977年访问过的天主教传教站。我认出了那些田地、大长屋或maloca的环境,以及河边的白沙滩,那里儿童和妇女在皮拉帕拉纳河的黑水中沐浴。但除此之外,一切似乎都非常不同。我记忆中那个相当悲伤、荒废的传教站已经消失了。在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晚上,一百多人聚集在大长屋里,男人们穿着羽毛盛装,跳舞、吟唱,服用神圣的药物——古柯和烟草、奇恰酒和死藤水。萨满们围在装着灵魂食物的葫芦旁,低声耳语,轻柔地吟唱咒语。我第一次听到了神圣的yurupari号角那令人难忘的声音,这是祖先在时间黎明时创造的。这些神话般的乐器长期被天主教神父谴责为魔鬼的象征,在传教站的岁月里被粉碎和焚烧。它们的声音仍然在这里,激励着新一代的巴拉萨纳人、马库纳人、塔图约人以及河流的其他民族,这有力地表明了文化仍然非常活跃。在我首次访问后的三十多年里,正如马丁所说,皮拉帕拉纳河上唯一消失的东西就是传教士们。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马丁、里卡多以及其他巴拉萨纳和马库纳领袖如马克西米利亚诺·加西亚和雷内尔·奥尔特加·加西亚的引导下,我们游历河流,参加仪式,拜访圣地——那些文化英雄与黑暗力量战斗并给世界带来秩序的急流,支撑天空的黑石穹顶,流淌着大母亲罗米·库穆经血的瀑布,她是大地的伟大母亲和始祖。在我们旅程过半时,斯蒂芬·休-琼斯飞来加入我们,他是剑桥大学前人类学系主任,与妻子克里斯汀在1960年代末首次生活在巴拉萨纳人中间。他现在作为受人尊敬的长者回到这里,是唯一能流利使用这种语言的学术学者。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和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民族志学者,斯蒂芬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理解巴拉萨纳人及其邻居的宇宙观。他的出现将这次旅程变成了一个关于精神和文化的持续教学,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启示,每天都带来对一种精妙哲学更深的理解,这种哲学在其复杂性上令人眼花缭乱,在其含义上充满深刻的希望。
在巴拉萨纳思想中没有开始和结束,没有时间、命运或宿命的线性进展感。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分形世界,其中没有事件有自己的生命,任何数量的思想都可以在平行的感知和意义层面上共存。规模屈服于意图。正如斯蒂芬告诉我的,每个物体都必须在各种分析层面上被理解。急流是旅行的障碍,但也是祖先的房屋,既有前门也有后门。凳子不是山的象征;它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座真正的山,萨满就坐在山顶上。一排凳子就是祖先的巨蟒,画在凳子木头上的图案既描绘了祖先的旅程,也描绘了装饰蛇皮的条纹。黄鹂羽毛的头冠真的就是太阳,每根黄色羽毛都是一道光芒。巴拉萨纳世界的无限元素在头脑中像旋转木马一样旋转,即使是适度尝试解释这些民族对生命意义的深刻直觉,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出发点——除了也许是大长屋maloca,它既是人们生活的物理空间,也是整个宇宙的宇宙模型。
如果文明的衡量标准(无论多么粗糙)是其纪念性建筑的规模——正如我们衡量印加人的石工、玛雅人的神庙——那么大长屋就是亚马逊古代民族惊人成就的证明。这些建筑巨大,其内部尺寸包罗万象。长度四十米,宽度可能二十米,拱形天花板在被一万次雷鸣般的舞步以及黎明时儿童安静走过而硬化的泥土地面上升到十米高,大长屋是亲族的子宫,氏族黑暗凉爽的庇护所,每一个精神的社会姿态都在其中发生并从中涌现的公共空间。
建筑的对称性精美绝伦:八根垂直柱子分两排均匀分布,门附近有两对较小的柱子,横梁,以及在椽子网格上编织的褶皱茅草排。房屋柱子以氏族祖先命名。前立面上的彩绘图案描绘了精神存在以及死藤水这种神圣制剂在头脑中释放的色彩和幻象图案。在世俗层面上,空间按性别划分,长屋前部留给访客和男人。这是社会轴线,在树脂和蜂蜡火炬的光焰中,古柯在夜晚准备,烟草以如此浓度服用,汗水流到指尖,世界疯狂旋转,但总是在和谐共鸣中。妇女控制空间的另一端,那里粘土烤盘放在世界的四个角柱上,木薯——一种致命的有毒植物——每天被母亲们转化为食物,人民的日常面包。维持生命的食物在其制备的某个阶段从精心编织的筛子中出现,筛子本身就是巨蟒的嘴。
maloca的屋顶是天空,房柱是支撑天空的石柱和群山。群山反过来是祖先存在的石化遗迹,是创造世界的文化英雄。较小的柱子代表原始巨蛇的后代。屋脊梁同时是太阳的轨道、天空的河流、银河、分隔生者与宇宙边界的动脉。地面是大地,在它下面流淌着冥界之河,死亡和悲伤的溪流。因此一条天河穿越天空,而它的反面,一条死亡的地下道路,穿越冥界。太阳每天从东到西穿越天空,每晚沿着冥界之河从西到东返回,那里是死者的地方。Barasana人将长者埋葬在maloca的地面上,用破碎独木舟制成的棺材。当他们进行日常生活时,生活在一个被真切地感知为其血统子宫的空间里,印第安人在祖先的物理遗迹上方行走。然而不可避免地,死者的灵魂会飘散而去,为了便于他们的离去,maloca总是建在靠近水边的地方。由于所有的河流,包括冥界之河,都被认为是向东流的,每个maloca都必须沿着东西轴线定向,两端各有一扇门,一扇给男人,一扇给女人。因此将maloca建在流水附近不仅仅是便利的考虑。这是承认生死循环的一种方式。水既回忆起创世的原始行为——巨蟒和神话英雄的河流旅程,也预示着衰败和重生的必然时刻。
如果长屋包围着社区,确保其永恒存在,庆祝其神话起源,大地本身则受到一个普遍的maloca保护,它悬浮在土地上方,由圣地锚定。Barasana人及其邻居的世界像女人用来制作木薯面包的陶烤盘一样平坦圆形。正如陶土块支撑着烤盘,真实的天空,宇宙maloca的屋顶,由一圈遥远的山丘支撑,其中有四个神圣的通道。北方和南方的门是肋骨门,将人类的身体与宇宙连接。西方的通道是痛苦之门,死者的命运,破坏力量进入并玷污世界的轴心。东方的水门通向乳河的河口,大地与天空融合、太阳诞生的起源点。对于Barasana和Makuna人来说,这些通道是真实的地方,与Ricardo Marin一起旅行时我们从空中看到了它们。世界始于Yuisi瀑布,终于Río Apaporis的Jirijirimo激流。沿着Taraira的山丘,Río Vaupés的Yurupari瀑布和Río Caquetá的Araracuara,Kanamari之外的山脊——这些都是物理起源点,一个写在大地上的神话地理。
在开始时,在季节创造之前,在祖先母亲Romi Kumu,女萨满,打开她的子宫之前,在她的血液和母乳产生河流、她的肋骨产生世界的山脊之前,宇宙中只有混沌。被称为He的灵魂和恶魔捕食自己的同类,无思考地繁殖,无后果地乱伦,吞噬自己的幼崽。Romi Kumu通过用火和洪水摧毁世界来回应。然后,正如母亲在烤盘上翻转温暖的木薯面包片一样,她将被淹没和焦烧的世界翻转过来,创造了一个平坦空旷的模板,生命可以从中再次涌现。作为女萨满,她然后生下了一个新世界:土地、水、森林和动物。
在一个平行的创世故事中,四个伟大的文化英雄——Ayawa,也被称为原始祖先或雷神——从东方沿着乳河而上,穿过水门,像犁一样推着神圣的Yurupari号角,创造峡谷和瀑布。河流从他们的唾液中诞生。被努力破坏的木片产生了最初的仪式器物和乐器。当Ayawa向世界中心旅行时,号角的音符带来了山脉和高地,宇宙maloca的柱子和墙壁。在每个转折点,Ayawa都面对贪婪的恶魔力量,渴求毁灭和觊觎世界的贪婪灵魂。通过智胜怪物,将它们变成石头,Ayawa为宇宙带来了秩序,使自然世界的精华和能量得以释放,造福所有有感知的生物和每种生命形式。然后,从女萨满的阴道中偷取创造之火,他们与她做爱,充分满足后,升入天堂成为雷电。
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女萨满向下游去东方的水门,在那里她生下了祖先巨蟒。随着时间推移,巨蛇追溯了Ayawa的艰难旅程,在身体和精神上回到河岸、瀑布和岩石,在那里它生下了Barasana、Makuna及其所有邻居的氏族祖先。每一个这些物理和地理的记忆点都保持着生机和活力,是神圣的联结点,Ayawa在那里向人类释放了生命的原始能量,甚至当他们将管理创造流动的永恒义务遗赠给所有巨蟒之民时。
因此,对于今天生活在Piraparaná森林中的人们来说,整个自然世界都充满了意义和宇宙学意义。每一块岩石和瀑布都体现着一个故事。植物和动物只是同一基本精神本质的不同物理表现。
与此同时,一切都比表面所见更为深邃,因为可见的世界只是感知的一个层面。在每一个有形的形式、每一株植物和动物背后,都有一个阴影维度,一个对普通人不可见但对萨满可见的地方。这是He灵魂的领域,一个神化祖先的世界,在那里岩石和河流都是活着的,植物和动物都是人类,汁液和血液是原始蟒蛇之河的体液。隐藏在激流中,在瀑布的物理面纱后面,在石头的正中心,是He灵魂的巨大maloca,那里一切都很美丽——闪闪发光的羽毛、古柯、装着烟草粉的葫芦,而烟草粉本身就是太阳的头骨和大脑。
萨满在仪式中前往的正是He灵魂的领域。与西方流行的传说相反,巴拉萨纳的萨满从不使用或操控药用植物。他的职责和神圣任务是在He的永恒领域中穿行,拥抱原始力量,并驾驭和恢复整个创造的能量。他就像一个现代工程师,进入核反应堆的深处来更新整个宇宙秩序。
在巴拉萨纳人中,这种更新是活人的根本义务。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巴拉萨纳人将大地视为充满力量的,将森林视为充满精神生物和祖先力量的活体。依靠土地生活就是拥抱其创造性和破坏性潜能。人类、植物和动物都有着相同的宇宙起源,在深层意义上被视为本质上相同的,对相同的原则做出回应,受相同的职责约束,对创造的集体福祉负责。自然与文化之间没有分离。没有森林和河流,人类就会灭亡。但没有人类,自然世界就没有秩序或意义。一切都将是混乱。因此,驱动社会行为的规范也定义了人类与野生世界互动的方式——与植物和动物、自然世界的多种现象、闪电和雷鸣、太阳和月亮、花朵的香气、死亡的酸臭味。一切都相互关联,一切都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神话为土地和生命注入意义,编码了在森林中生存所必需的期望和行为,将每个社区、每个maloca都锚定在深刻的地方精神上。
这些宇宙观念在生态学上有着非常现实的后果,无论是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在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方面。森林是男人的领域,花园是女人的领域,在那里她们既孕育植物也孕育孩子。女人们种植三十多种食物作物,并促进大约二十种野生水果和坚果的繁殖力和丰产性。男人们只种植烟草和古柯,他们将这些植物种在蜿蜒穿过女人田地的狭窄小径上,就像草中的蛇一样。对于女人来说,收获和准备木薯——这种日常面包——的行为是一种生育的姿态和一种启蒙的形式。在磨碎的浆糊完全冲洗后剩下的淀粉液体被视为女性的血液,可以通过加热使其安全,并像母乳一样温热地饮用。粗糙的木薯纤维类似于男人的骨骼。在平底锅上烤制,由女性的双手塑形,木薯是野生植物精神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被驯化的媒介。像所有食物一样,它具有矛盾的潜能。它给予生命,但也可能带来疾病和不幸。因此,除非食物经过长者的手,并由萨满祝福和精神净化,否则什么都不能吃。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物就是力量,因为它代表着能量从一种生命形式向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转移。随着孩子的成长,他或她只是慢慢地接触新的食物类别,而严格的食物限制标志着生活的所有重要转折——男性的启蒙时刻、女性的初潮、过渡时刻,在这些时刻,根据定义,人类与He的精神领域接触。当男人去森林打猎或捕鱼时,这从来不是一次琐碎的行程。首先,萨满必须在恍惚中旅行,与动物的主人协商,与精神守护者建立神秘的契约,这种交换总是基于互惠。巴拉萨纳人将其比作婚姻,因为狩猎也是一种求爱形式,在其中人们寻求更高权威的祝福,以获得将珍贵生物带入自己家庭的荣誉。肉类不是猎人的权利,而是来自精神世界的礼物。未经允许的杀戮会冒险被精神守护者杀死,无论是以美洲豹、蟒蛇、貘还是鹰雕的形式。森林中的人总是既是捕食者又是猎物。维护相邻人类部族之间和平与尊重的那些谨慎而既定的社会协议,促进仪式物品、食物和女性交换的协议,同样适用于自然。动物是潜在的亲属,正如野生河流和森林是人类社会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人类学家卡伊·阿尔赫姆(Kaj Arhem)所写,所有这些观念和限制创造了本质上是由神话启发的土地管理计划。例如,在巴拉萨纳人(Barasana)和马库纳人(Makuna)可获得的四十五种猎物中,只有二十种被定期狩猎。在大约四十种鱼类中,也许只有二十五种被食用。复杂的食物限制导致了高度多样化的生存基础,这种基础集中在食物链的低端。貘虽然备受珍视,但很少被狩猎,无论如何都为长老保留。肉类总体而言,虽然对猎人的身份认同很重要,但作为蛋白质来源远不如鱼类或昆虫重要。蚂蚁、幼虫和白蚁,以及木薯面包,是既美味又高度精致的饮食和烹饪的基础。由于河流中几乎每一个弯道和急流、每一个溪流交汇点和每一块石头都与神话事件相关联,整个景观都在萨满的心中绘制成图。猎人避开盐舔处。在被祖先之血污染的地方禁止捕鱼,这些海滩和侧水道也恰好是萨贝尔塔鱼(sabelta)或帕洛美塔鱼(palometa)的产卵栖息地。皮拉帕拉纳河(Piraparaná)的整段河流,栖息着数百种鱼类,因精神原因被视为禁区。萨满的制裁,虽然受宇宙观启发,但确实减轻了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实际效果。由于启发这些信仰的神话事件是持续进行的,其结果是一种活生生的哲学,真正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体。
这一切在仪式中变得生动起来。在离开皮拉帕拉纳河之前,我们参加了为纪念木薯女神(Cassava Woman)而举行的生育仪式,这个活动持续了两天两夜,吸引了来自河流上下游的数百名男女和家庭前往奥尔特加港(Puerto Ortega)的大屋(maloca)。我们的主人是雷内尔·奥尔特加·加西亚(Reinel Ortega García),一位巴拉萨纳萨满。大屋的酋长是帕特里西奥(Patricio);他的妻子罗莎(Rosa)是木薯女神,生育和延续的象征。所有等级制的领导都到位了——吟诵者和舞者、智慧守护者和酋长、萨满和库穆(kumu),即祭司。斯蒂芬·休-琼斯(Stephen Hugh-Jones)用一个奇特的比喻描述了这些不同宗教人物的角色。他说,萨满就像外交部长;他横向处理与自然力量的关系。与此同时,库穆或祭司,纵向地,通过时间,与祖先打交道。他不即兴发挥。他的语言,如同颂歌一样,是礼拜仪式的、古老的,除了那些被教授其内在含义的人之外,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是深刻宗教知识的经典,他不会偏离或即兴发挥。这样做就像天主教神父改变圣体礼拜的语言和祈祷一样不合适。
奉献的强度在负责编织羽毛冠冕用于舞蹈的男人身上最为明显。他们在大屋中被隔离了几个星期,禁止吃肉或鱼,或与妻子在一起。为了制作灿烂的黄色羽毛,他们从活鸟身上拔取羽毛,并将青蛙毒液和有毒浆果的膏体涂在鹦鹉的胸部,使新羽毛从通常的深红色变成太阳的颜色。这些装饰不是装饰性的。它是与神圣空间的字面连接,是通向神圣的翅膀。
随着仪式开始,时间坍塌了。有两系列舞蹈,被一天中的临界时刻——黎明、黄昏和午夜——所分隔。在穿上羽毛,纯洁思想的黄色冠冕,雨的白鹭羽毛时,男人们成为了祖先,就像河流是蟒蛇,山脉是世界的房柱,萨满是变形者,在一刻是掠食者,下一刻是猎物。他从鱼变成动物再变成人类,然后再次变回,超越每一种形式,成为在现实的每一个维度之间流动的纯能量,过去和现在,这里和那里,神话和世俗。他的颂歌逐一回忆蟒蛇祖先之旅中遇到的每一个地理要点,这些地名可以完全准确地追溯到亚马逊河以东1600多公里处,那里曾经繁荣着伟大的文明。
里卡多告诉我,白人用眼睛看,但巴拉萨纳人用心灵看。他们既前往时间的黎明,也进入未来,拜访每一个神圣地点,向每一个生物致敬,因为他们庆祝自己最深刻的文化洞察——认识到动物和植物只是现实另一个维度中的人。这就是巴拉萨纳哲学的精髓。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告诉我们这种文化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基于通过时间和激烈的祭司研究和启蒙获得的知识的传统。地位归于智慧之人,而非战士。他们的大屋在宏伟程度上可以与人类伟大的建筑创作相匹敌。他们对天文学有复杂的理解,太阳历法,强烈的等级制和专门化概念。他们的财富投资于与中世纪宫廷一样优雅的仪式装备。他们的交换系统,无限复杂,促进和平,而非战争。他们为宇宙带来秩序、维持生命能量流动的斗争,以及他们信仰和适应的特异性,留下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可能性,即巴拉萨纳人是曾经存在的世界的幸存者——那些令加斯帕·德·卡瓦哈尔(Gaspar de Carvajal)和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Francisco de Orellana)如此震惊的复杂社会和酋长制,亚马逊失落的文明。
也许,在巴拉萨纳人和马库纳人以及所有水蟒之民的适应和文化生存中,我们能够窥见那些信念和信仰,这些信念和信仰曾经让无数人能够沿着世界上最伟大河流的河岸生活。当今天的巴拉萨纳人参与仪式并服用yagé这种令人惊奇的药剂时,他们说自己穿越多个维度,重温阿亚瓦的旅程,降临在神圣的地点,完成所有这些非凡的精神行为,这是因为他们确实做到了。当我们说巴拉萨纳人及其邻居既回响着古代前哥伦布时期的过去,又指向未来的道路,体现了人类社会如何能够在亚马逊盆地生活和繁荣而不破坏森林的模式时,这是因为他们确实能够做到。
“直觉的心智是神圣的礼物,理性的心智是忠实的仆人。我们创造了一个尊崇仆人却忘记礼物的社会。”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偏远地区崎岖的山结中,坐落着一个被第一民族称为神圣源头的绝美山谷。在那里,在加拿大塞伦盖蒂——斯帕齐荒野的南缘,三条加拿大最重要的鲑鱼河流在极其相近的地方发源:斯蒂金河、斯基纳河和纳斯河。在漫长的一天里,也许两天,人们可以穿过开阔的草地,沿着灰熊、驯鹿和狼的足迹行走,从激发了太平洋西北地区众多伟大文化——基特桑人和韦茨乌韦滕人、卡里尔人和塞卡尼人、奇姆申人、尼斯加人、塔尔坦人、海斯拉人和特林吉特人——的三条河流的源头饮水。再继续三天,你就能到达芬利河的源头,这是加拿大最伟大河流——麦肯齐河的源头。
我所知道的唯一另一个有如此地理奇观的地方是西藏,在冈仁波齐峰的山脚下涌现出亚洲三条大河——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这些重要动脉为下游超过十亿人带来生命。受到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崇敬,冈仁波齐峰被认为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有人被允许踏上其山坡,更不用说攀登到顶峰。用工业开发破坏其山坡的想法,对所有亚洲人民来说都代表着超越所有想象的亵渎行为。任何胆敢提出如此行为的人都将面临最严厉的制裁,无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来世。
在加拿大,我们对待土地的方式截然不同。违背所有第一民族的意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开放神圣源头进行工业开发。这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倡议。帝国金属公司提议在托达金山山坡建设一个露天铜金矿,每天处理30,000吨矿石,而托达金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羊种群之一的栖息地。如果建造,其尾矿池将直接排入伊斯库特河源头湖链,伊斯库特河是斯蒂金河的主要支流。在其二十五年的生命周期中,该矿将产生1.83亿吨有毒尾矿和3.07亿吨废石,需要进行超过200年的酸性排水处理。另外两家矿业公司——财富矿物有限公司和西鹰开发公司——将以类似规模撕裂源头山谷本身,用露天无烟煤开采作业夷平整座山峰。
最大的项目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提议从同一无烟煤矿床中提取煤层气(CBM),覆盖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巨大区域。如果这一开发项目继续进行,将意味着在整个神圣源头盆地的景观上铺设由数千口井组成的网络,通过道路和管道连接。据所有报告,CBM回收是一个高度侵入性的过程。为了从无烟煤中释放甲烷,技术人员必须用大量化学试剂在高压下压裂煤层,一次注入超过一百万升,这种技术在某些矿床中释放出大量高毒性水。超过900种不同的化学品,其中许多是强致癌物,被登记使用,但出于专有权考虑,公司不必披露在任何给定地点使用的溶液身份。
撇开环境问题不谈,想一想这些提议对我们文化的意味。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为正常:那些从未踏上土地、对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或联系的人,可以合法地获得进入的权利,并且由于其企业的本质,在其身后留下完全改变和亵渎的文化和物理景观。更重要的是,在授予此类采矿特许权时,通常最初以微不足道的金额给来自遥远城市的投机者,给那些历史比我的狗还短的拼凑公司,我们对土地本身没有赋予文化或市场价值。摧毁自然资产的成本,或其完整保留的内在价值,在支持荒野工业化的经济计算中没有衡量标准。没有公司必须为其对公共财产——森林、山脉和河流——所做的事情向公众赔偿,这些按定义属于每个人。只要有收入流和就业的承诺,就只需要获得许可即可进行。我们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是我们制度的基础,是商业在资源驱动经济中提取价值和利润的方式。但如果你仔细想想,特别是从如此多其他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化受到对生活和土地完全不同愿景的触动和启发——这似乎是非常奇怪和高度异常的人类行为。
在马西讲座的第四讲中,我想反思我们这种特殊的态度,即我们将地球简化为商品、随意消费的原材料的方式。在此过程中,我将怀着希望地建议,正如人类学视角所揭示的,实际上存在许多其他选择,有无数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在地点和景观中定位自己。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地理和生态空间中安身立命的多种方式反映了,正如托马斯·贝里神父如此美妙地写道,无限与不可能、纯真与世俗、神圣与肮脏,这些都代表着地球独特的梦想。
在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启蒙运动期间,在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中,我们欧洲传统将人类心灵从绝对信仰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个体从集体中解放出来,这在社会学上等同于分裂原子。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也放弃了许多对神话、魔法、神秘主义,也许最重要的是隐喻的直觉。宇宙,十七世纪的勒内·笛卡尔宣称,仅由”心灵和机制”组成。用一句话,除了人类之外的所有有知觉的生物都被去活化了,地球本身也是如此。“科学”,正如索尔·贝娄所写,“对信仰进行了大扫除。”无法被积极观察和测量的现象不能存在。到了十九世纪,实证主义传统甚至定义了社会研究,随着社会科学的发明,这是一个矛盾的词汇表达。世俗物质主义的胜利成为了现代性的自负。土地可能有灵魂(anima),鹰的飞行可能有意义,精神信仰可能有真正共鸣的观念,被嘲笑、被驳斥为荒谬。
几个世纪以来,理性思维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科学这一它最精妙的表达,在其所有的辉煌中仍然只能回答”如何”这个问题,但永远无法接近解决终极问题:“为什么”。科学模型的固有局限性长期以来引发了某种存在主义困境,这对许多从童年起就被教导宇宙只能被理解为微小原子粒子在空间中旋转和相互作用的随机行为的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更重要的是,将世界简化为机制,将自然仅视为要克服的障碍、要开发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文化传统盲目地与生活着的地球互动的方式。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长大,被教育相信雨林存在是为了被砍伐。这就是我在学校学习并在森林中作为伐木工实践的科学forestry意识形态的本质。轮伐周期——全省森林被砍伐的速度,因此也是可持续产量forestry的基础——基于所有原始森林都将被砍伐并替换为人工林场的假设。forestry学术学科的语言本身就是虚假的,仿佛是为了误导而构想的。“年度允许砍伐量”不是永远不能超过的限制,而是要达到的配额。“下降效应”,即随着原始森林枯竭而计划中的木材产量下降,被推广为自然现象,但正如伐木营地的每个人都承认的,这是一个惊人的承认,即自1940年代实施现代forestry以来,森林每年都被严重过度砍伐。“多用途forestry”,暗示森林要为各种目的进行管理,始于皆伐。原始森林被采伐,尽管它从未被种植,也没有人期望它重新生长。古老森林被描述为”衰败”和”过度成熟”,而按照任何生态学定义,它们正处于最丰富和生物多样性最强的阶段。这些稀有而非凡的雨林的内在价值,就像神圣源头的山脉和草地的固有价值一样,在规划过程的计算中没有位置。
这种文化视角与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的观点截然不同,那些在欧洲接触时生活在温哥华岛上的人们,以及仍在那里的人们。如果我被送到森林去砍伐它,一个相似年龄的夸夸嘉夸(Kwakwaka’wakw)青年传统上在他的哈马察(Hamatsa)启蒙仪式中被派遣到同样的森林中去面对胡克斯胡克夫(Huxwhukw)和天空弯喙(Crooked Beak of Heaven),生活在世界北端的食人精灵,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胜利地返回到夸富宴(potlatch),使他的个人精神纪律和坚韧可能用野性的能量重新振兴他的整个民族。重点不是问或建议哪种观点是对还是错。森林仅仅是纤维素和板英尺吗?它真的是精灵的领域吗?山是神圣的地方吗?河流真的沿着巨蟒(anaconda)的祖先路径流淌吗?谁能说呢?最终这些不是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是信念的力量,即信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决定了一种文化的生态足迹,即任何社会对其环境的影响。一个被教育相信山脉是保护神居所的孩子,将与一个被教育相信山脉只是等待开采的惰性岩石块的年轻人截然不同。一个被教育要敬畏沿海森林为神圣领域的Kwakwaka’wakw男孩,将与一个被教导相信这些森林注定要被砍伐的加拿大孩子不同。一种文化的全部意义既包括人们的行为,也包括他们抱负的品质,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隐喻的性质。
也许,这里蕴含着许多原住民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本质。生活在新几内亚的疟疾沼泽中,西藏的寒风中,撒哈拉的酷热中,几乎没有感伤的余地。怀旧并非因纽特人的常见特征。婆罗洲的游牧狩猎采集者对他们缺乏技术能力去破坏的山地森林并没有自觉的管理意识。然而,这些文化所做的,是通过时间和仪式与大地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基于对土地的深深依恋,还基于更加微妙的直觉——即土地本身是通过人类意识呼吸而生的理念。山川、河流和森林不被视为无生命的,不是人类戏剧上演舞台上的简单道具。对这些社会而言,土地是活的,是一种被人类想象力拥抱和转化的动态力量。这种归属感和连接感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脊梁和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的高处得到了最完美的阐述,后者是一个孤立的山体,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平原上方高耸约6000米。而它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极其精妙的哲学中找到了也许最抽象和最具影响力的表达。这些是我想在本次讲座中探索的地方。
我第一次南行穿越安第斯山脉是在1974年春天,当时作为一名年轻学生,我有幸加入了一个植物学考察队,任务是揭开一种被印加人称为”不朽神圣之叶”的植物的奥秘——古柯,这是臭名昭著的可卡因来源。这是一项非凡的任务。可卡因于1855年首次从叶子中分离出来,它通过允许无痛摘除白内障而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特别是眼科学。它至今仍是我们最强大的局部麻醉剂。叶子的精华仍然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增添风味:古柯使可口可乐成为”真正的东西”。这家软饮料公司反过来为制药业提供今天医学界使用的所有合法可卡因。
到1970年代中期,拉美贩毒集团正在崛起,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如何崛起,也没有人意识到他们会变得多么肮脏和血腥。当时的非法贸易仍掌握在独立流浪者手中。根除传统种植园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但这些误导的清洗与可卡因无关,而与那些敬畏这种植物的人们的文化认同有关。特别是利马的医生们,他们对安第斯山脉原住民的关心程度只能与他们对印第安人生活的无知程度相匹配,他们在1920年代向山区望去,看到了可怕的贫困、糟糕的卫生和营养状况、高文盲率、婴儿死亡率和疾病。他们寻求解释。土地分配、经济剥削和债务奴役制度持续存在的真正问题挑战了他们自己阶级结构的基础,所以他们将古柯定为罪魁祸首。每一个可以想象的社会弊病和病态都被归咎于这种植物。根除传统种植园成为国家优先事项,在1940年代后期联合国的干预下,成为国际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这种公众关注和歇斯底里,1974年人们对这种植物的科学了解却很少。驯化物种的植物学起源、叶子的化学成分、咀嚼古柯的药理学、植物在营养中的作用、栽培品种的地理分布、野生和栽培物种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仍然是谜团。当然,人们普遍承认,古柯在安第斯山脉受到的敬畏程度是其他植物无法比拟的。在印加时代,如果祈求者口中没有古柯,就无法接近任何神圣的神殿。由于无法在帝国首都库斯科的海拔高度种植古柯,印加人用金银复制了这种植物,在为景观着色的仪式田地中。直到今天,高原地区没有古柯叶的能量与大地母神Pachamama精华的相互交换,就不会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没有神圣植物的调解,就不能种植或收割任何田地,不能将任何孩子带到世界上,也不能引导任何长者进入死者的领域。
令美国政府某些部门沮丧的是,我们团队于1975年对这种植物进行了首次营养研究,发现的结果令人震惊。该植物含有少量生物碱,大约占干重的0.5%至1%,这种温和的浓度通过脸颊粘膜被温和地吸收。但它还含有大量维生素,钙含量比美国农业部研究过的任何植物都高,这使其非常适合传统上缺乏乳制品的饮食。研究还表明,叶子产生的酶能增强身体在高海拔地区消化碳水化合物的能力,这对安第斯山脉以马铃薯为主的饮食来说是理想的。这一科学发现清楚地凸显了至今仍在进行的根除传统种植田的严厉措施的荒谬性。古柯不是毒品,而是一种神圣的食物,安第斯人民将其作为温和的兴奋剂温和使用了4000多年,没有任何毒性证据,更不用说成瘾性了。
以古柯为镜头,当代泛安第斯世界的丰富性慢慢进入了我的视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抵达秘鲁引发了一场灾难,但从那次可怕的接触中产生了一种非凡的文化融合,至今仍从基督教和古老的前哥伦布信仰中汲取灵感。征服者竭尽全力粉碎安第斯的精神,摧毁了所有的宗教寺庙和圣像。但每当西班牙人在被拆毁的神殿上竖起十字架或建造教堂时,在人民眼中这只是确认了该地固有的神圣性。因为印第安人崇拜的不是建筑物,而是土地本身:河流和瀑布、岩石露头和山峰、彩虹和星辰。五百年的欧洲统治,伴随着各种不公正,却未能平息安第斯的本质冲动,这种冲动至今仍能在每个村庄和山谷中感受到,在羊驼和骆马放牧的高原草丛中,在失落帝国每个城市和十字路口的石砌街道上。
在南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之间,如今有600万人以克丘亚语——印加人的语言——作为母语。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对世界的贡献包括马铃薯和西红柿、烟草、玉米、奎宁和古柯。对他们来说,土地是真正活着的。山脉是神秘的存在,它们聚集雨水、创造天气、为土壤带来肥力、为田野带来丰收,或者在愤怒时播下破坏和混乱,释放致命的暴风雨或霜冻,能在瞬间摧毁一年的劳作,就像1983年发生的那样,十五分钟的冰雹摧毁了广阔库斯科地区的整个玉米作物。
南安第斯的每个社区至今仍由特定的保护山神——阿普(Apu)主导,它指引着那些在其阴影下出生的人的命运。因此,人们至今每走一步都在穿越他们认为神圣的土地。正如传统农业经济仍然基于劳动力交换,互惠也定义了社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这些仪式义务和关系从不被谈论,也从不被遗忘。大地母亲(Pachamama)和阿普们会养育人民,只要人们反过来以适当的关怀和敬意对待它们。
当男男女女在小径上相遇时,他们会停下来交换古柯的k’intus,三片完美的叶子排列成十字形。转身面向最近的阿普,他们将叶子举到嘴边轻吹,这是一种仪式性的祈求,将植物的精华送回大地、社区、神圣的地方和祖先的灵魂。交换叶子是一种社交姿态,一种承认人类联系的方式。但轻吹——称为phukuy——是一种精神互惠的行为,因为无私地给予大地,个体确保古柯的能量终将回归,就像落在田野上的雨水终将重生为云朵一样确定。这种微妙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祈祷,在年度以社区为基础的承诺和参与仪式中得到盛大庆祝。
我对安第斯的了解大部分是在钦切罗学到的,这是库斯科郊外一个极其美丽的山谷。城镇中心坐落在图帕·印加·尤潘基的夏宫遗址上,他是伟大的印加统治者中的第二位。精美的梯田延伸至翠绿的平原,这是古代海床的底部,向北上升至维尔卡班巴的遥远山峰——帝国的最后堡垒。向东,安塔基尔卡——神圣的阿普——起伏的山坡主导着天际线。坐落在遗址高处的是殖民时期的教堂,1981年我在那里为一个可爱的男婴阿曼多担任教父,与他的家庭建立了至今仍然兴旺的友谊。
每年在钦切罗,在雨季的高峰期,会发生一件非凡的事件:mujonomiento,一年一度的边界巡跑。每个小村庄中跑得最快的男孩在这一天被赋予荣誉,成为异装者,即waylaka。穿着姐妹或母亲的服装,手持白色仪式旗帜,waylakas必须带领所有身体健康的男性进行奔跑。行程距离仅有30公里,但路线要穿越两个高耸的安第斯山脊。奔跑从海拔3500米的村庄广场开始,穿过废墟下降300米到达Antakillqa山脚,然后上升约900米到达山脊顶峰,再下降到远侧的山谷,接着再次攀登到达分水岭的草地和回家的漫长小径。这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朝圣,因为边界由土堆标记,这些是神圣的场所,人们在此祈祷,向大地献上古柯,向风献上酒水,waylaka必须跳舞,在有节奏的旋涡中旋转,将女性精髓和远在下方村庄中留守妇女的能量吸引到神圣的山峰。每一个仪式动作,奔跑者都在声称对大地的所有权。这是本质的隐喻。一个人作为个体开始这一天,但通过疲惫和牺牲(sacrifice)——一个源于拉丁语”使神圣”的词——一个人融入到单一社区的脉搏中,这个社区通过仪式性的虔诚宣告了其归属感,并确保了其在神圣地理中的位置。
朝圣,穿越景观走向神性的阴影,自有记忆以来就是安第斯生活的核心特征。为了献祭,印加祭司攀登到海拔6500米的山峰顶,这个高度在欧洲传统中400年后才能达到。在征服之后,这些朝圣继续进行,随着基督教的注入呈现出新的共鸣和形式,但始终植根于古老的景观和神秘力量观念。像钦切罗的mujonomiento这样的本地化庆典包含了与伟大的泛安第斯朝圣相同的主题元素,这些朝圣即使在今天仍吸引着来自整个南安第斯地区社区的数万人。
在第一次与waylakas一起奔跑边界大约一年后,我与我的好朋友尼尔达·卡拉纳乌帕(Nilda Callañaupa)和来自钦切罗的一大群人一起前往西纳卡拉(Sinakara)神圣山谷,这里是Qoyllur Rit’i节,即星雪节的举办地,这也许是所有安第斯朝圣中最艰苦和最具精神启发性的朝圣。它位于库斯科正东约130公里处,从路径起点需要6小时车程,目的地是一个高海拔天然圆形剧场,一个位于海拔约4750米的翠绿盆地,由科尔奎彭库(Colquepunku)冰川的三条舌状冰舌主导,像祭坛一样面对着山谷。根据天主教信仰,18世纪晚期在西纳卡拉发生了一个奇迹,一个小男孩看到了基督的耀眼幻影。在这个地点建造了一座神庙,主的形象至今仍可在石头中看到。
对于印加人来说,这块岩石已经是神圣的,整个山谷也是如此。对他们而言,物质是流动的。骨头不是死亡而是结晶的生命,因此是强大的能量源,就像被闪电充电的石头或被太阳带入存在的植物。水是蒸汽,但在其最纯净的形式中,它是冰,是山坡雪地的形状,是朝圣者最高和最神圣目的地的冰川。山脉被称为Tayakuna,即父亲们,其中一些如此强大,以至于甚至看它们都可能是危险的。其他神圣场所,如洞穴或山口或瀑布——那里奔腾的水声如神谕般说话,被尊为Tirakuna。这些不是居住在地标内的灵魂。相反,敬畏的是这些实际场所本身。河流是大地的开放血管,银河是它们的天体对应物。彩虹是双头蛇,从神圣的泉水中出现,横跨天空,再次埋入大地。流星是银色的闪电。在它们后面是所有的天空,包括宇宙尘埃的黑暗斑块,负星座,对于高原人民来说,这些与在天空中形成动物的星团一样有意义。
印加人认为库斯科是世界的肚脐。太阳神庙科里坎查是轴心,从这里向地平线的各个方向辐射出四十一条概念线,它们的排列由星辰和星座、太阳和月亮的升降决定。沿着这些视线或ceques,有数百个神圣地点,每个都有自己的庆祝日,每个都由特定社区敬奉和保护。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和每个氏族,虽然根植于特定的地方,却都与帝国的宇宙学框架相连。这些神龛或huacas——就像西纳卡拉的神圣石头,基督在西班牙人镇压印加人最后一次大起义后仅两年就奇迹般地、颇为方便地出现在那里——是神圣道路上的驿站,这些道路在字面和形而上的意义上都存在。在重要时刻,如夏至或印加皇帝逝世时,祭司们会要求献祭。被选中的人,被太阳祝福的儿童和动物,会从帝国各地被召唤到库斯科。一些在首都被杀;另一些被选中将部分祭祀血液带回各自的社区,在那里他们最终也会被杀。随行队伍通过道路抵达库斯科,但在离开时他们沿着ceques的神圣路线,直线行走越过山脉和河流,有时要走数百公里,拜访当地神龛,向他们命运的完美致敬。这些旅程,就像儿童的献祭一样,让人民与印加重新联合,象征性地代表了帝国对安第斯山脉险峻地形的胜利。
位于库斯科正东方的西纳卡拉山谷充满着形而上的力量。它向西开放到奥桑加特山的侧翼,奥桑加特是所有Apus中最重要的。通过ceque线在宇宙学的空间和时间中与库斯科对齐,它也标志着帝国四个象限中两个象限的边界,被称为”Tawantinsuyu”,即世界的四个区域。南方和东方是科拉苏约,包含玻利维亚的高原、的的喀喀湖和所有太阳之山。北方和东方是安蒂苏约,云雾森林和热带低地,是他们世界中从未被印加完全征服的已知部分。因此,印加宇宙学和思想中的核心对立——上与下、山与林、文明与野蛮——在朝圣者从地平线各方抵达西纳卡拉向Qoyllur Rit’i之主致敬时的仪式中得到体现。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西纳卡拉山谷和圣所都寂静而孤独,只有偶尔的牧羊人造访。但在升天节和圣体节这两个移动节日之间的三天里,当昴宿星团——七姐妹星——在夜空中重新出现时,通常在六月的前几天,多达四万名朝圣者聚集在山脚下,有些步行到达,有些骑骡子,还有些乘坐敞篷卡车和公共汽车。从路尽头的小村庄开始,朝圣者的狭窄队伍缓慢地沿着一条持续攀升九公里的小径前进,这条路线有石祭坛和石堆标记,是十字架的驿站,男男女女在这里停下祈祷和献供。每人都携带一束小石头,象征着罪恶的重担,随着接近山谷一块一块地减轻。在西边天际线上方盘旋着奥桑加特的山峰。南安第斯的所有社区都有代表——来自保卡尔坦博的丛林舞者、来自普诺和的的喀喀湖的群体、安塔平原、库斯科和乌鲁班巴圣谷的人们。骡子和驴子运送食物和供给;所有人都必须步行,甚至是残疾人,他们拖着残破的身体一寸一寸、一步一步地爬上小径。
在海拔4750米处,即使有明亮的阳光,空气也很寒冷,但几小时后到达的西纳卡拉却因众多信徒的存在而感到温暖。气氛既热烈又深沉,是色彩、祈祷、舞蹈和歌唱的盛典。仪式旗帜和彩旗装饰着山坡,在风中似乎在振动。沿着谷底,每个社区都划定自己的地盘,十几种色调的毯子和斗篷形成了一张铺在滋养每个人的小溪两边的拼布被。丛林战士或chunchus戴着饰有鹦鹉羽毛的头饰,穿着用胭脂虫染成深红色的束腰外衣。山脉在pablitos或ukukus中得到体现,这些来自所有高地社区的蒙面男子,数百个打扮成熊的小丑,负责维持和平、控制人群并执行最重要的仪式。这些山脉和丛林的象征性化身进行模拟斗争,戏剧性的场面回忆着古老的战斗,无论真实还是想象的,以及安第斯生存的两个对立极点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当男人们舞蹈、虚张声势、摆姿势时,女人们聚集在圣所内,那里被成千上万根蜡烛的光芒照亮,许多蜡烛有高个孩子那么高。黄昏时,一层烟雾笼罩着草地。有铜管乐队、长笛、竖琴和鼓的持续嘈杂声,舞者的高假声,以及烟花的爆炸声。三天三夜没有人睡觉。大地因舞者的动作和仪式队伍缓慢的悸动节拍而颤抖。
在欢庆和虔诚之下,仪式有着极其严肃的目的。山神可能愤怒或仁慈。冰雪既是力量之源,也是疾病的瘴气。冰川是令人恐惧的领域,不是因为任何物理危险,尽管朝圣者每年确实会死于寒冷和暴露,而是因为它们是condenados的居所——那些被诅咒到时间尽头的灵魂。根据印加神话,ukuku是女人和熊的后代,一种超自然的生物,拥有独特的力量来对抗和击败condenados。因此,他们必须用高亢的叫声和面具,来执行Qoyllur Rit’i最危险和庄严的行为。就像基督自己一样,他们必须承担十字架的重负。当朝圣者的队伍抬着圣人雕像穿过山谷时,ukukus在月光守夜后,从他们村庄的教堂举起十字架,抬着它们爬上Colquepunku山坡800米,将它们插在冰川中,让山和大地的能量为其充电。然后,在第三天黎明前,他们用鞭子绳索相连,爬回冰上取回十字架,而在远处下方,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跪下默默祈祷。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山顶,向山神致敬。
在西方,Ausangate是第一座被黎明光芒照亮的山峰。光线慢慢沿着山坡移动,逐渐填满下面的山谷。太阳升起后,十字架被取下,由ukukus背着穿过Sinakara,通过山口,进入将把它们带回村庄的卡车。人们还从山上带来冰块,这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虔诚的循环:人们前往山的高处祈祷并向神灵致敬。以冰的形式,山的精华回到山谷,为田野带来生命和肥沃,为家庭带来福祉,为动物带来健康。这是人民、山峰和神灵之间活生生的动态关系,一个相互信任和更新的三位一体,一个为整个泛安第斯世界文化生存的集体祈祷。
Qoyllur Rit’i节的活力和权威,其仪式的象征共鸣和意义,它向年轻人传达的教训,预示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同时也促进对过去和印加遗产更深刻的理解。
当我从Sinakara回到库斯科时,我和另一位朋友Johan Reinhard一起,他是我小女儿的教父,沿着神圣山谷前往马丘比丘。作为一名登山家和高海拔考古学家,Johan已经攀登了大约200座5000米或更高的安第斯山峰,寻找前哥伦布时期仪式埋葬和祭祀的证据。1995年,在Ampato峰顶附近,在大多数人几乎无法呼吸的海拔高度,他发现了”冰女”——500年前被祭祀的少女完美保存的木乃伊遗骸,由此载入史册。Johan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安第斯山脉土地与文化通过时间的关系。当他第一次遇到遗址时,他的目光立即转向天际线和神圣的山峰。通过在地理中寻找线索,在山脉和河流的方向中,在天体的运动中,在今日景观中明天考古学的配置中,他能够解开南美洲最传奇考古遗址的谜团。
1911年当Hiram Bingham发现马丘比丘时,他著名地将其描述为”失落的城市”。实际上,这个建筑群一直是印加帝国的组成部分,明确连接到通往库斯科的道路网络,延伸4万公里,将美洲历史上最长的帝国联系在一起。位于乌鲁班巴河上方的战略高地,马丘比丘处于完美位置,既能守卫通往神圣山谷的通道,同时又能控制Antisuyo的东部低地——古柯、药用植物和萨满灵感的来源。这确实是一个仪式中心,建立为Pachacuti的皇室庄园,他是锻造了一个延续不到一个世纪帝国的三位伟大印加统治者中的第一位。对运河和水道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马丘比丘是根据单一建筑计划建造的,正如Johan确定的那样,这个计划本身是在印加宇宙学框架内构思的,并植根于古代安第斯神圣地理的概念。设计这个建筑群的人攀登了周围的每一座山峰,建造了高高的观测平台,日夜观察山峰的位置和星座的运动。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简单的工程。山神影响并启发了印加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土壤的肥沃和雨水的可预测性,到军队的成功以及太阳王及其姐妹王后的福祉和生育力。
印加帝国最神圣的两座山峰是Ausangate,如我们所见,它俯瞰着Qoyllur Rit’i山谷,以及位于马丘比丘正南方的Salcantay。马丘比丘的实际守护神(Apu)是瓦伊纳比丘(Huayna Picchu),这座标志性的圆锥形山峰主宰着整个遗址。马丘比丘的神圣中心是Intihuatana,这是一块奇特的雕刻石头,宾汉称之为”太阳的拴马柱”。约翰是第一个注意到Intihuatana回响着瓦伊纳比丘的形状的人,而且石头上全天的光影变化也复制了瓦伊纳比丘上阴影的涨落。就在Intihuatana南面几步之外,有一座石刻的低矮祭坛。在瓦伊纳比丘的山顶上有一座形状相同的孪生祭坛。约翰观察到,从山顶发出的直线南北方位线平分了Intihuatana和两座祭坛,并继续向南穿透整个地区主要山峰Salcantay的心脏。瓦伊纳比丘、Intihuatana和Salcantay形成了完美的南北对齐。当南十字星座升到天空的最高点时,它正好坐在Salcantay的山顶上。被银河包围的南十字星座是印加人最重要的星座之一。这个发现使约翰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乌鲁班巴河(Urubamba River),对印加人来说,这条河是银河在地上的对应物。像蛇一样,乌鲁班巴河蜿蜒围绕着马丘比丘,然后流向亚马逊。在神话中,这是维拉科查(Viracocha)在创世之初行走的大道,他沿着这条路创造了宇宙。
但乌鲁班巴河源于何处?在Ausangate的山麓,今天它主宰着Qoyllur Rit’i的遗址。正如Salcantay融化的雪花为马丘比丘带来生命,俯瞰Sinakara的冰川冰雪今天仍在为安第斯山脉的人民带来灵感。西班牙征服五百年后,这些古老的神圣地理观念继续定义和滋养着社会存在,将生者与死者、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正如印加时代一样。
如果说在南安第斯山脉,这些原初的直觉可以在仪式中感受到,从五个世纪基督教影响和统治的熔炉中提炼出来,那么在南美洲有一个地方,前哥伦布时代的声音仍然直接而纯粹,不受任何过滤器的束缚,只有世界缓慢转动的影响。在这个血染的大陆上,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的印第安人从未被西班牙人完全征服。他们是一个叫做泰罗纳(Tairona)的古代文明的后裔,今天大约有30,000人,科吉人(Kogi)、阿瓦科人(Arhuacos)和维瓦人(Wiwa)很久以前就逃脱了死亡和瘟疫,定居在一个高耸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平原6,000米之上的山间天堂。在那里,经过500年的时间,他们受到了一个全新的地球之梦的启发,这个启示确认了永恒法则的存在,这些法则平衡了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巴洛克式潜能与自然的所有力量。这三个民族,语言不同但在神话和记忆上密切相关,共享着相同的适应方式和基本的宗教信念。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忠于他们古老的法则——Serankua和伟大母亲的道德、生态和精神教条——并且仍然由mamos祭司阶层领导和启发。他们明确相信和承认自己是世界的守护者,他们的仪式维护着生命的平衡和繁衍。他们完全了解他们共同的祖先泰罗纳人在1591年对入侵者发动了激烈但徒劳的战争。在他们的山区据点中,消失在历史中至少三个世纪,他们故意选择将自己的文明转变为和平的虔诚文化。
当mamos(或祭司)说话时,他们立刻显示出他们的参照点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提到哥伦布,就好像他的到来是最近的事件。他们谈论伟大母亲,就好像她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她确实活着,在他们的aluna概念中每时每刻都在共鸣和显现,这个词译为水、土地、物质、生殖精神、生命力。重要的,具有终极价值的,赋予生命目的的不是被测量和看见的东西,而是存在于aluna领域的东西,意义的抽象维度。九层宇宙、九层神庙、孩子在母亲子宫中度过的九个月都是神圣创造的反映,每一个都启发着其他的。因此,藤蔓也是蛇,山脉是宇宙的模型。阿瓦科男子戴的圆锥形帽子代表神圣山峰的雪原。人体上的毛发呼应着覆盖山坡的森林树木。自然的每一个元素都充满了更高的意义,以至于即使是最普通的生物也可以被视为老师,最小的沙粒也是宇宙的镜子。
在这个宇宙图式中,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人类的心灵和想象力,伟大母亲才能显现。对内华达山脉的印第安人来说,人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他们称自己为长兄,认为他们的山脉是”世界的心脏”。我们这些因对神圣法则无知而威胁地球的外来者被贬为幼弟。
在许多方面,Kogi族、Arhuacos族和Wiwa族的故乡确实是世界的缩影,因此在象征意义上是世界的心脏。圣玛尔塔雪山(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是地球上最高的沿海山脉。在地质上与哥伦比亚东部与委内瑞拉边境的安第斯山脉没有连接,它作为自己的构造板块漂浮着,呈三角形轮廓,每边150公里,虽然附着在南美大陆上,但被四周的裂谷与大陆分离。该山体由35个主要流域排水,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在50公里内从海平面上升到雪峰。在其起伏的褶皱和深谷中,几乎可以找到地球上所有主要生态系统的代表。沿海有珊瑚礁和红树林沼泽,西侧山坡有热带雨林,北部有沙漠,东部有干旱灌木林,在云雾和风雨中高耸的是高山苔原和雪原,祭司们在那里祈祷和献祭。靠近赤道,日夜各十二小时,雨季和旱季各六个月,圣玛尔塔雪山是一个平衡和谐的世界——印第安人坚持认为,这正是伟大母亲(Great Mother)所期望的样子。
根据神话,当伟大母亲纺织她的思想并构思出宇宙的九个层次时,山脉被梦想出来。为了稳定世界,她将纺锤插入世界的轴心并抬起山体。然后,解开一段棉线,她勾勒出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在雪山山脚周围画了一个圆圈,宣布这里是她孩子们的故乡。
这一原始的创世行为永远不会被遗忘。织布机、纺纱行为、社区编织进景观结构的概念,对于雪山的人们来说是重要而生动的隐喻,自觉地指导和引导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作为农民生存,为了利用不同的生态区域,他们不断迁移,在炎热的低地收获木薯、玉米、咖啡、糖和菠萝,在云雾林的寒冷薄雾中种植土豆和洋葱,攀登得更高放牧牛群和采集茅草。他们将这些周期性的迁徙称为线索,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在大地上铺下了保护斗篷。当他们建立花园时,女性通过种植平行于地块边缘的行列来播种南半部分。男性负责北半部分,建立垂直于女性所种行列的行列,这样两半部分如果重叠就会产生一块织物。花园就是一块布。当人们祈祷时,他们在手中握着小束白棉花,这是教会他们纺纱的伟大母亲的象征。祈祷时手的圆形运动回忆起伟大母亲将宇宙纺织成形的时刻。她的诫命是保护她编织的一切。这就是她的法则。
那些负有引导全人类遵循Serankua之道责任的人是mamos(祭司),他们的宗教训练是严格的。年轻的侍僧在幼年时就被带离家庭,然后在黑暗的阴暗世界中被隔离,在kan’kurua(男性神庙)内或其附近环境中待十八年——两个九年的时期,明确回忆母亲子宫中九个月的孕期。在整个启蒙过程中,侍僧们都在伟大母亲的子宫中,在所有这些年里,世界只作为抽象概念存在。他们在神圣领域中被文化化,学习只有他们的仪式和祈祷才能维持世界的宇宙和生态平衡。经过艰苦的转变后,年轻人被带去朝圣,从海洋到冰川,从云雾林穿过岩石和草丛到páramo(世界之心的门户)。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看到世界不是作为抽象概念,而是以其令人震撼的美丽真实存在的样子。信息很明确:这是他要保护的。
从海岸他携带棉花、贝壳和热带植物的果荚到高山圣湖制作pagamientos(献祭品),在那里风是伟大母亲的呼吸,精神守护者居住在那里,他们有责任执行她的法则。供品保护生命的所有表现形式。朝圣者的纯洁思想如种子一般。从páramo,他收集草药和espeletia的叶子带回海边,这种植物在西班牙语中被称为”修道士”,因为从远处看它可能被误认为是人的轮廓,一个在旋转的云雾中迷失的游荡僧侣。朝圣,在景观中的移动,对于长兄(Elder Brothers)来说是一种持续的肯定姿态,将人类和自然结合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中。
自哥伦布以来,雪山的人们惊恐地看着外来者违背伟大母亲,砍伐他们认为是她身体皮肤和织物的森林,建立外来作物的种植园——香蕉和甘蔗、大麻,现在是古柯用于非法生产可卡因。被古柯贸易的利润吸引,被军队追捕,左翼游击队和右翼准军事组织进入雪山并包围了印第安人。对长老们来说,这种来自下方的危险与来自高处的威胁相呼应。雪山的雪原和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退缩,改变着山地生态。对我们来说,这些可能看起来是完全无关的发展。但对长老们来说,它们与彼此以及与年轻兄弟(Younger Brothers)的愚蠢行为密不可分,是世界末日的预兆。
当我上次在Sierra时,我与Arhuacos人一起陆路旅行,这次旅程从他们的主要中心Nabusimake开始,进行了仪式净化,然后前往圣湖并返回大海。与我同行的是Danilo Villafaña,他是我的老朋友Adalberto的儿子,后者被准军事组织谋杀。Danilo如今是Arhuaco的政治领袖,但我记得当他还是婴儿时,我曾背着他在当时和平的Sierra Nevada山坡上上下下。暴力一直是Danilo生活的背景,数十名Kogis人、Wiwas人和Arhuacos人被FARC(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杀害,被准军事组织屠杀,或在军队的交火中丧生。但印第安人仍然坚持和平。正如Danilo在我们坐在Nabusimake的小溪边时对我说的:“精神世界、mamos的世界和枪支的世界是不相容的。”
当我从朝圣之旅返回时,我与备受尊敬的Wiwa mamo Ramon Gill交谈。“祖先说,”他告诉我,“总有一天小弟弟会醒来。但只有当自然的暴力降临到他身上时。那时他才会醒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会战斗。我们只想让人们理解。我们在这里平静地说话,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
2004年1月9日,在国际可卡因消费引发的暴力高潮时期,在经历了两年期间Sierra地区数百名印第安男女死亡(包括许多mamos)之后,Kogi人、Wiwa人和Arhuaco人发表了联合声明:“谁将为我们呼吸的空气、流动的水、太阳的光芒向宇宙母亲付费?存在的一切都有神圣的灵魂,必须受到尊重。我们的法律是起源的法律,生命的法律。我们邀请所有小弟弟成为生命的守护者。我们确认对母亲的承诺,并呼吁所有民族和国家团结统一。”
令人谦卑的是,即使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长兄们的mamos,生活在距离迈阿密海滩仅两小时航程的地方,正从Sierra Nevada的高处凝视着大海,为我们和整个地球的福祉祈祷。
听到这样的叙述,人们的倾向是将其视为无可救药的天真或美好得不真实而不予理睬。可悲的是,这往往是我们对遇到但不理解的文化的反应,这些文化的深刻复杂性如此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让人不知所措。当英国人到达澳大利亚海岸时,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复杂性,无法拥抱其奇迹。他们不了解沙漠的挑战,对土著人民的成就缺乏敏感性——土著人民在超过55,000年的时间里,作为狩猎采集者和世界守护者而繁荣发展。在那段时间里,改善自然世界、驯服野性节奏的愿望从未触及他们。土著人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一个宇宙整体,第一个黎明的不变创造,当时天地分离,原始祖先彩虹蛇带来了所有原始祖先,他们通过思想、梦境和旅程歌唱出世界的存在。
祖先们一边歌唱一边行走,当该停下来时,他们就睡觉。在梦中,他们构思第二天的事件,创造的节点融合在一起,直到每个生物、每条溪流和石头、所有空间和时间都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伟大的原始冲动的神圣显现。当他们因劳作而疲惫时,他们退入大地、天空、云朵、河流、湖泊、植物和动物中,这个岛屿大陆至今仍回响着他们的记忆。祖先们走过的道路从未被遗忘。它们是歌路(Songlines),即使今天人们穿越物理世界的模板时仍遵循的精确路线。
当土著人追踪歌路并吟诵第一个黎明的故事时,他们成为祖先的一部分并进入梦境时代,这既不是梦也不是时间流逝的度量。它是祖先的真实境界,一个平行宇宙,普通的时间、空间和运动定律不适用,过去、未来和现在融为一体。这是欧洲人只能在睡眠中近似体验的地方,因此早期英国定居者将其称为梦境(Dreaming)或梦境时代(Dreamtime)。但这个术语具有误导性。按西方定义,梦是一种与现实世界分离的意识状态。相比之下,梦境时代是真实世界,或者至少是土著人日常生活中体验的两种现实之一。
沿着歌路行走就是成为世界持续创造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既存在又仍在形成中。因此,土著人不仅仅依附于大地,他们对其存在至关重要。没有土地他们会死去。但没有人民,持续的创造过程将停止,地球将枯萎。通过运动和神圣仪式,人民保持对梦境时代的接触,并在祖先的世界中发挥动态和持续的作用。
一个时刻始于虚无。一个男人或女人行走,从空虚中涌现出歌声,现实的音乐化身,赋予世界特性的宇宙旋律。歌声创造振动,振动成形。舞蹈为形式带来定义,现象学领域的物体出现:树木、岩石、溪流,所有这些都是梦想时光(Dreaming)的物理证据。如果仪式停止,声音沉寂,一切都将失去。地球上的一切都由歌线(Songlines)连接在一起,一切都从属于梦想时光,它是恒定的但又在不断变化。每个地标都与其起源的记忆结合,但又总是在诞生。每个动物和物体都与远古事件的脉搏产生共鸣,同时仍被梦想到存在中。现存的世界是完美的,尽管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土地编码了曾经存在的一切,将要存在的一切,在现实的每个维度中。行走在土地上就是参与一个持续的肯定行为,一个无尽的创造之舞。
十八世纪最后几年冲上澳大利亚海滩的欧洲人,缺乏语言或想象力,甚至无法开始理解土著人深刻的智慧和精神成就。他们看到的是一群生活简单的人,其技术成就有限,面孔看起来奇怪,习惯令人费解。土著人缺乏欧洲文明的所有标志。他们没有金属工具,对书写一无所知,从未屈服于种子的崇拜。没有农业或畜牧业,他们不产生盈余,因此从未接受定居的村庄生活。等级制度和专业化是未知的。他们的小型半游牧群体,生活在用树枝和草搭建的临时住所中,依靠石制武器,体现了欧洲对落后的观念。对英国人来说,特别是一个民族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想象的。时间的进步和改善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是维多利亚生活的基本精神。在欧洲人眼中,土著人是野蛮的化身。一位早期的法国探险家将他们描述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最接近野兽的人类”。
“他们不过是狗而已,”威廉·耶茨牧师在1835年回忆道,“射杀他们并不比射杀一只对你吠叫的狗更有害。”为了合理化大量使用鞭子,西澳大利亚的一位早期定居者指出,“应该记住,土著人有兽皮,而不是像普通人类那样的普通皮肤。”被射死后,土著人的尸体被用作稻草人,软绵绵的尸体挂在树枝上。“他们的命运,”安东尼·特罗洛普在1870年写道,“就是被灭绝,越快越好。”直到1902年,一位当选的政治家金·奥马利在议会中起立宣布:“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土著人是人类。”
根据1936年《土著人管理法》的规定,西澳大利亚没有土著人可以在没有国家许可的情况下移动。任何土著父亲或母亲都不被允许拥有孩子的合法监护权。土著人可以被命令进入保留地和机构,或被驱逐出城镇。政府对任何婚姻的合法性都有最终决定权。直到1960年代,一本学校教科书《澳大利亚动物宝库》仍将土著人列为该国比较有趣的动物之一。
到二十世纪初,疾病、剥削和谋杀的结合使土著人口从欧洲接触时的一百多万人减少到仅仅三万人。在一个多世纪里,一块由歌线连接的土地,人们可以轻松地从一个维度移动到另一个维度,从未来到过去,从过去到现在,从伊甸园转变为末日战场。
了解我们今天对土著人心灵的非凡广度、他们思想和哲学的微妙,以及他们仪式的启发力量,令人不寒而栗地想到这个人类潜能、智慧、直觉和洞察力的储库,在那些可怕的死亡和大火的日子里几乎枯竭。事实上,土著语言在接触时可能有270种,可能有600多种方言,现在正以每年一种或更多的速度消失。一半已经失传,今天只有18种语言被多达500个人说。
事实上,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幻象领域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伟大实验之一。作为第一批离开非洲的人类后代,澳大利亚的第一批人类来到了一个在地理上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了一亿多年的岛屿大陆。他们遇到了一个严酷而不可能的地方,地球上最干燥的陆地,进化本身在这里发生了奇特的转折,产生了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的植物和动物:产卵的哺乳动物、巨大的不会飞的鸟类,以及一系列在有袋动物育儿袋安全环境中在子宫外哺育胚胎的生物。在土著人看到的第一批动物中,也许甚至在海上的一次公开横渡中,是8米长的咸水鳄鱼,这些原始生物几乎完全潜在水中时也能看见、听见和呼吸。这些爬行动物以隐蔽方式狩猎,杀死任何它们能制服的东西,并会欢迎,尽管不是热情地,一种新的猎物形式。
一旦上岸,人们就开始徒步迁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型大家庭群体到达了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建立了氏族领地,这些领地通过共同语言松散地联合成更大的网络或部落。氏族领地的大小取决于土地的承载能力。南部和东部的草原和桉树林拥有相对较大的人口集中。中部和西部的沙漠人烟稀少,以至于人们如同沙地上的影子。到欧洲人接触时,有多达10,000个不同的精神和社会焦点领域,10,000个家园,每一个都被培养成战士的男孩们积极保卫着。
氏族的边界,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由圣地、连接人们和祖先的叙述以及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定义,西方人类学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开始绘制其复杂性。有一百多种命名的亲属关系,每一种都暗示着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血缘和婚姻的规则和法规建立了一个社会地图,让每个人随时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行为。澳大利亚原住民没有技术巧术(这是我们的伟大成就),而是发明了一个连接性矩阵。通过这样做,他们产生了一个保护壳,它与我们出于类似动机建造的城墙一样令人敬畏、令人安慰和完整,用来隔离我们的生活免受自然变迁的影响。
在氏族领地内,个人发展出了对地方的局部化知识,这是非凡的。我最近与一个杰出的人奥托·布尔曼尼亚·坎皮恩(Otto Bulmaniya Campion)和他的大家庭——他的妻子克里斯汀(Christine)、他的叔叔杰弗里(Geoffrey)、所有的孩子们——在澳大利亚北领地阿纳姆地(Arnhem Land)的偏远地区度过了一个月。我想了解梦幻时代(Dreaming)和歌路(Songlines),比我从书本中学到的更多。起初我询问问题,寻求定义,但后来,意识到我的愚蠢,我只是观察。
到达一个比拉邦(billabong)——一个池塘或沼泽,一个露营的地方时,奥托和小伙子们立即点燃草地,既为了净化也为了再生这个地点。当他们洗澡时,他们拍打水面,向鳄鱼传递信息。然后他们用铁木树枝的烟雾净化自己,并用双手在每棵树的树干周围包上一圈泥土和红赭石。通过几个手势,他们驯化了这个空间,用树枝清扫地面,建立防风屏障,从melaleuca树上剥下大片纸皮作为被褥和毯子。母亲和幼儿睡在一个圆圈里,长者男性睡在另一个圆圈里,年轻的单身男孩睡在第三个圆圈里。当他们捕捉barramundi鱼时,他们保持着持续的对话,描述他们饥饿和需求的性质,祈求祖先和鱼类祖先的精神。食物他们称之为”bush tucker”,可以是任何东西——绿蚂蚁、飞狐、鹅或野薯。当他们狩猎时,他们用泥土覆盖身体,掩盖气味,与猎物合为一体。一天早上,克里斯汀和奥托的儿子用红赭石画自己,这是一个仪式契约,允许男孩转变成彩虹蛇(Rainbow Serpent)的形象。
夜晚围着篝火,奥托与他父亲的精神对话,那是从火焰中传来的声音。白天他用强烈的演绎逻辑追踪袋鼠,这会让夏洛克·福尔摩斯都感到羞愧。但一旦动物死了,他就恢复到敬畏状态,严格的协议精确地规定了尸体必须如何处理,否则最可怕的灾难将降临到猎人和他的社区。舌头被小心地取出,这样孩子们就能学会正确和尊重地说话。腿在膝盖处折断以释放动物的精神,然后按特定的顺序和方式折叠和绑定。内脏被切开以显露寄生虫,生吃,只用从胃中提取的绿色粗饲料调味。肉类的分配反映了亲属关系的权威:头部给猎人,尾部给姐夫,后腿给二兄弟和三兄弟。
当我们一起走过这片土地时,我不仅为奥托知识的深度感到震惊,更为他的认知方式感到震惊。他的思维完全是非线性的,一种似乎是自由联想的魔法模式。一列蚂蚁会引向汗蜂,从地下挖出的蜂蜜引起对神话鸟类的提及,谈论精神,这反过来又把我们带回到晨星歌路(Morningstar Songline)、岩袋鼠梦幻(Rock Wallaby Dreaming)和纸皮树的用途——庇护所等等的来源。木棉树开花意味着小袋鼠或小袋鼠仔有足够的毛发在母亲死后生存。一棵未知树木上的黄红色花朵,颜色暗示着鸸鹋脂肪,向奥托透露了捕猎长颈龟的合适时间。
通过与奥托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我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原住民从来不是真正的游牧民族。相反,他们被锁定在由祖先划定的领地内。这是一个启示。想象一下,如果所有在你之前的世代的天才和智慧都集中在一套任务上,专门专注于了解一块特定的土地,不仅是植物和动物,而且是每个生态、气候、地理细节,每个有感知生物的脉搏,每一阵风的节奏,每个季节的模式。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常态。
连接氏族领土的不是人们的物理迁移,而是一个共同理念的力量,一种微妙而普遍的哲学,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是梦创时代(Dreaming)。正如我们所见,它在一个层面上指的是最初的黎明,当时彩虹蛇和所有祖先生灵创造了世界。这在歌径(Songlines)中被铭记,歌径是这些祖先在唱出世界时所走过的轨迹。
但是,我从奥托那里了解到,歌径并不是直线或线性的。它们甚至不一定存在于三维空间中。然而,在数量上,它们编织出一张覆盖整个大陆的网络。对于一个缺乏文字的文明来说,它们成为了过去的记录、未来的承诺,以及在当下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正如奥托教导我的,个人的目标不是从头到尾跟随歌径,而是在标记歌径穿过自己特定氏族领土的力量和记忆点上向祖先致敬。
但是,关键的是,梦创时代不是神话或记忆。它是在创世时发生的事情,但也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将在永恒中发生的事情。在土著宇宙中没有过去、现在或未来。在接触时刻所说的数百种方言中,没有一种有表示时间的词汇。没有线性进步的概念,没有改进的目标,没有对变化可能性的理想化。相反,梦创时代的整个逻各斯(logos)就是静止、恒定、平衡和一致性。人类的整个目的不是改进任何东西。而是参与被认为对维持世界至关重要的仪式和礼仪活动,使世界完全保持在创世时刻的状态。想象一下,如果所有西方的智识和科学热情从时间开始就专注于保持伊甸园完全像亚当和夏娃进行那次决定性对话时的样子。
土著人民的宇宙并非理想世界。冲突是暴力的。仪式可能极其严酷。以沃尔皮里人(Warlpiri)为例,获得启蒙知识涉及切割和改造男性性器官,垂直切开最终使阴茎完全张开。但正如W.E.H.斯坦纳(Stanner)所描述的,这个文明的主导情绪是对信仰的接受。怀疑、质疑或异议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正如他所写的,梦创时代”定义了存在的,决定了现在的,体现了所有可能的”。
在西方传统中,存在是需要思考的。我们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走出生活之外,去辨别我们定义为洞察的抽象理念。梦创时代使这种反思既无意义又不可能。它将个体包围在一个信仰和信念的网络中,没有出口,因为人无法认为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违反梦创时代的法则是一种不限于当下的违背,而是一种在所有维度中回响的违背,穿越永恒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正如斯坦纳所理解的,土著人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他写道,他们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战胜了历史的文明。
梦创时代回答了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它规定了一个人必须生活的方式。人的义务不是改进自然,而是维持世界。土地的实际保护是每个土著男女最根本的优先事项。这是一种深刻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不是在说它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但它有后果。显然,如果整个人类都遵循土著人的方式,遵循这些第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类后裔所铺设的智识轨道,我们就不会把人送上月球。但另一方面,如果梦创时代成为普遍的信仰,我们今天就不会思考那些按任何科学定义都威胁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工业过程的后果。
这个故事,就像所有叙述一样,蜿蜒回到起点。我在这次讲座的开头谈到了圣源地(Sacred Headwaters),这个令人惊叹的美丽而珍贵的山谷瑰宝,鲑鱼河流从这里诞生,这些河流流向家园——实际上是我的家园,因为斯蒂金河(Stikine)是我居住的地方。斯蒂金河谷的人民,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非凡的地方之一,已经团结起来反对这些项目,因为他们对土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对他们来说,圣源地是一个社区,既是他们的杂货店和圣所,也是他们的教堂和校园,他们的墓地和乡村俱乐部。他们相信对山谷拥有最大所有权的人是尚未出生的世代。圣源地将是他们的摇篮。伊斯库特(Iskut)长老们,几乎所有人都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已经正式呼吁结束山谷中的所有工业活动,并创建一个圣源地部落遗产区。
自2005年夏天以来,伊斯库特的男女老少,连同来自电报溪和更远地方的塔尔坦族和第一民族支持者,在所有季节都在通往圣源头地唯一道路入口处维持着一个教育营地。那些想要亵渎他们托管土地的人被拒绝入内。那些接受并敬畏这片土地本来面貌的人则受到欢迎。他们与每个人分享着对其家园以及该省整个西北象限可持续管理新时代的愿景。经过这么多年的坚守,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最终,关键在于整个北美最非凡地区之一的未来。圣源头地的命运超越了当地居民、省级机构、矿业公司以及那些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工业开发的少数人的利益。再多的甲烷气体、煤炭或铜矿都无法补偿一个可以成为所有加拿大人乃至全世界人民圣源头地的地方所付出的牺牲。这最终就是长老兄弟们传达的信息。
“技术进步崇拜中隐含的为所有人建立单一文明的理想使我们变得贫乏和残缺。每一种消失的世界观,每一种消失的文化,都减少了生命的一种可能性。” —— 奥克塔维奥·帕斯
伊甸园已经被发现,它位于非洲西南海岸,距离朱瓦西布须曼人的家园不远,他们世代与卡拉哈里的狮子保持着公开的休战。人类从非洲出发的起点也被相当精确地定位,在这个古老大陆的另一边,红海西岸。从那里我们穿过沙漠和雪覆盖的山口,穿过丛林和山涧,最终跨越海洋和被风吹蚀的珊瑚环礁,来到面向整个大陆的黑沙海滩,那里充满了无尽的神秘和潜在的希望。我们定居在北极和喜马拉雅,亚洲草原和北方针叶林,那里冬风如此猛烈,柳树汁液都会结冰,驯鹿在阳光照不到的枯枝上觅食。在印度的河流上,我们遇到了回响人心的声音,在撒哈拉的炽热寂静中我们找到了水。一路上我们发明了一万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在墨西哥瓦哈卡的山区,马萨特克人学会了通过口哨声进行远距离交流,模仿他们声调语言的语调,创造出写在风中的词汇。在达荷美海滩上,伏都教修行者敞开了神秘主义的窗户,发现了恍惚的力量,让人类能够轻易且无害地进出精神领域。在云南的森林中,纳西萨满将神秘故事刻在岩石上,而在奥里诺科河三角洲,瓦劳人中的对应者忍受尼古丁中毒,寻求异象和灵感,了解雨神、燕尾鸢之屋、纹章猛禽和舞蹈美洲豹的知识。
在苏门答腊附近的西贝鲁岛上,门塔威人认识到精神赋予一切存在的生命——鸟类、植物、云彩,甚至横跨天空的彩虹。这些神圣的实体在世界的美丽中欢欣鼓舞,不可能被期望居住在一个本身不美丽的人体中。因此门塔威人开始相信,如果自然失去光泽,如果景观变得单调,如果他们自己作为造物中的物理存在不再向美的本质致敬,造物的原始力量就会抛弃这个领域,前往死者的居所,所有生命都将灭亡。为了尊重祖先和颂扬生者,门塔威人,无论男女,都将生命奉献给对审美之美的追求,梳理身体,磨锐牙齿,在头发上添加绚烂羽毛,在身体上刻印精美的螺旋图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全身装饰地处理每一项任务,无论多么平凡。
在日本京都外的山区,天台宗僧侣每天只睡两小时,仅以一碗面条和一个饭团为食,在神圣的日本柳杉林中连续奔跑十七小时,持续七年,在他们的回峰行修行中一度每天跑80公里,持续一百天。作为最后的考验,他们必须在九天内不吃不喝不睡,即使在静坐冥想时,身体也暴露在篝火的炽热中。传统规定,那些未能完成训练的人必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白袍下携带着刀和绳子。背上挂着草鞋。他们一天要磨坏五双。在过去四个世纪中,只有四十六人完成了这种磨难,这是一条让修行者更接近死亡领域的启蒙仪式之路,其目标是向生者揭示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平等的,人类并不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人们经常问为什么这些奇妙而异域的文化及其信仰体系的消失会有影响。对于温哥华或哈利法克斯的家庭,对于萨斯喀彻温省农场或生活在纽芬兰湾拥抱和安慰中的人来说,如果非洲某个遥远部落通过同化或暴力而灭绝,如果他们通过仪式表达的梦想和精神激情化为乌有,这有什么重要性?正如你可能猜到的,如果你有机会思考这些马西讲座的前四讲,这个疑问让我困惑。如果有人需要问这个问题,他或她可能被期望理解答案吗?
魁北克人民是否关心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失去他们的文化?可能不会。正如魁北克的消失对图阿雷格人来说也无关紧要一样。但我认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对整个人类都很重要。一方面,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谁能说加拿大人的现实观比图阿雷格人的更重要?在更根本的层面上,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大多数加拿大人永远不会遇到穿着蓝袍的图阿雷格人驼队缓缓穿过白沙海洋的景象。同样,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看到莫奈的画作,或听到莫扎特的交响乐。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这些艺术家和文化及其对现实的独特诠释,世界不会变得更加贫乏?
所以我用生物学的比喻来回应。如果一个物种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好吧,想象你正要登上飞机,你注意到机修工正在拆除机翼上的铆钉。你问了显而易见的问题,机修工说:“没问题。我们每拆一个铆钉都能省钱,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也许失去一个铆钉没有什么区别,但最终机翼会掉下来。文化也是如此。如果马拉松僧侣停止奔跑,或者如果门塔威(Mentawai)的孩子们将他们的美感转向更加平凡和缺乏灵感的东西,或者如果纳西萨满不再在石头上书写并放弃他们的本土文字东巴文——世界上最后一种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天会塌下来吗?不会。但我们谈论的不是单一物种的消失或单一文化适应的丧失。我们说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毁灭瀑布。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人类一半的声音正在被消音。
问题不在于变化。我们在西方有这样的自负,认为当我们在庆祝和发展技术奇迹时,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不知何故一直是静态的和智力懒惰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真相了。变化是历史上唯一不变的常数。所有地方的所有民族总是在与生活的新可能性共舞。技术本身也不是对文化完整性的威胁。拉科塔人(Lakota)放弃弓箭使用步枪时并没有停止成为苏族人,正如来自Medicine Hat的牧场主放弃马车使用汽车时并没有停止成为加拿大人一样。威胁文化完整性的既不是变化也不是技术。而是权力,统治的粗暴面孔。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这些土著民族,这些遥远的他者,尽管他们可能古怪而多彩,但不知何故注定要消失,仿佛受自然法则支配,仿佛他们是现代化的失败尝试,是成为我们的失败尝试。这根本不是真的。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都是被可识别和压倒性的外部力量驱逐出存在的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民族。这实际上是一个乐观的观察,因为它表明,如果人类是文化毁灭的推动者,我们也可以成为文化生存的促进者。
为了获得对这种权力与文化冲突的视角,让我们暂时转向我们自己大陆的历史和一个第一民族——基奥瓦人(Kiowa)的经历。基奥瓦人最初是来自密苏里河源头的狩猎采集民族,大约在美国革命前一个世纪从山区下到达科他的草原。他们遇到了克劳人(Crow),克劳人教给他们平原的宗教和文化,太阳的神性,野牛的方式,马匹的力量和用途。他们后来向北迁移到黑山(Black Hills),在那里与拉科塔人作战,然后向南逃跑,被夏安人(Cheyenne)和阿拉帕霍人(Arapaho)驱赶穿过阿肯色河的源头。在那里,基奥瓦人与科曼奇人(Comanche)发生冲突,然后结成联盟,使两个民族控制了南部草原和像阴影一样在大陆上移动的庞大野牛群。
每年一次,在夏季的高峰期,当棉白杨树上出现绒毛时,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太阳舞,这是精神复兴的时刻。帐篷搭成一个宽阔的圆圈,整个营地都面向升起的太阳。药物小屋是焦点,因为在其中,在西侧竖立的一根棍子上,悬挂着Tai-me,太阳的神圣形象。这是一个简单的护身符,一个小人形,有着绿石的脸,白羽毛的长袍,和貂皮头饰以及一根直立的羽毛。它的脖子上挂着蓝色珠子串,在它的脸、脖子和背部绘有太阳和月亮的符号。对基奥瓦人来说,Tai-me是生命本身的源泉。它被保存在生皮盒子里,由世袭的守护者保护,除了太阳舞的四天外,它从不暴露在光线下。在那时,它的力量传播到在场的所有人和一切:孩子们和武士舞者,躺在其底部作为动物太阳代表的野牛头骨,在它面前展示的十个药物包,四天四夜缓缓转动盾牌跟随过往太阳的男人们,整天每天凝视太阳牺牲自己视力以使人民能够看见的年轻舞者。
直到1871年,北美的野牛数量仍然超过了人口。那一年,人们可以站在达科他州的悬崖上,向四周50公里的范围内都能看到野牛。兽群规模如此庞大,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全部通过。怀亚特·厄普曾描述过一个超过百万头动物的兽群,分布在相当于罗德岛州面积大小的放牧区域内。在那次目击后的九年内,野牛就从大平原上消失了。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消灭野牛,摧毁平原文化。今天被环保主义者推崇的西奥多·罗斯福表达了当时的民族情绪:“定居者和开拓者站在正义一边;这片伟大的大陆不能仅仅作为肮脏野蛮人的狩猎保护区而存在。”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系统性的屠杀将野牛数量减少到了动物园里的珍奇动物程度,并摧毁了所有土著人的抵抗。策划这场战役的菲利普·谢里丹将军建议美国国会铸造一枚纪念奖章,一面是死野牛,另一面是死印第安人。1890年7月20日,太阳舞被正式取缔,基奥瓦人和所有平原文化的人们在监禁威胁下被禁止进行他们最基本的信仰仪式。1892年春天爆发的麻疹和流感给了他们最后一击。
在美国边疆发生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有重演。1879年在阿根廷,罗卡将军发起了”征服沙漠”军事行动,其明确目标是消灭潘帕斯地区的印第安人并夺取他们的土地和牲畜。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在接触后的75年内被完全消灭。基督教传教士约翰·韦斯特牧师将这场屠杀合理化为对土地的必要清洗,清除他所描述的”令人憎恶的梦魇”般的冒犯性民族。1850年,法属波利尼西亚殖民政府作为原则正式禁止了所有波利尼西亚文化表达形式,包括岛屿间贸易和航行、仪式祷告和盛宴、纹身、木雕、舞蹈,甚至歌唱。1884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取缔了夸富宴(potlatch)。一年后,当欧洲代表聚集在柏林会议瓜分非洲大陆时,他们正式承诺支持所有”旨在教育土著民并教导他们理解和欣赏文明益处”的努力。导致1892年《布鲁塞尔法案》的后续会议呼吁世界各地的殖民强国”消除野蛮习俗”。
同年,在西北亚马逊地区普图马约河(Río Putumayo)沿岸,第一批4万名博拉族和惠托托族印第安人死亡,他们被英秘橡胶公司的贸易商和监工杀害。在刚果自由邦,利奥波德国王的私人军队同样为了追求乳胶——森林的白色血液,屠杀了多达800万非洲人。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这场全球冲突摧毁了欧洲青年,违背了一切体面和荣誉的概念——战胜者聚集在巴黎,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的条款,将部落民族、所有那些无法承受”现代世界严酷条件”的人置于他们的监护之下,作为”文明的神圣托管”。在战争之前的一百年里,土著民族被迫向殖民强国交出了跨越近半个地球的土地。数百万人死亡,成为那个文明的受害者——而这个文明在其自我毁灭的痉挛中,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两次几乎烧毁了整个世界。
这种剥夺的遗产,正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说的”风的世纪”,提醒我们这些命运攸关的事件并非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而是在我们祖父母的有生之年,并且至今仍在继续。种族灭绝,即对一个民族的肉体消灭,受到普遍谴责。文化灭绝,即对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破坏,在许多地方却被认可和支持为适当的发展政策。现代性为剥夺权利提供了理由,而真正的目标往往是从被土著民族世代居住的领土上工业规模地开采自然资源,他们在土地上的持续存在被证明是一种不便。
巴拉姆河口呈现出大地的颜色。向北,沙捞越的土壤消失在南中国海中,成队的日本空货船悬浮在地平线上,等待潮汐和机会用从婆罗洲森林中撕扯出来的原木装满船舱。河流定居点是机遇与绝望并存的场所——泥泞的伐木营地和成群的棚屋,它们麻风病般的外观用金属片、塑料和拾来的木板拼凑修补。河边的孩子们倾倒成桶的垃圾,这些垃圾在每艘过往原木驳船的尾流中又漂回岸边。河流被碎片和淤泥堵塞了几公里,沿岸堆放着数千根原木,叠放30层深,有些等待装运,有些在热带高温中慢慢腐烂。
距离上游约150公里处是另一个世界,这是一片多样而神奇的森林和高山景观,被水晶般清澈的河流分割,布满了世界上最广泛的洞穴和地下通道网络。这里是本南人(Penan)的传统领土,这是一个狩猎采集文化,常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后的游牧民族之一。在神话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颂扬森林的丰饶,这片森林的生物丰富性和多样性甚至超过了亚马逊最繁荣的地区。在婆罗洲林地总面积仅为一平方公里的一系列地块中,面积不到温哥华史丹利公园的四十分之一,发现的树种数量竟与整个北美洲的树种数量相当。
游牧这个术语有些误导性,暗示着一种不断迁徙的生活,也许还暗示着对地方缺乏忠诚。事实上,本南人穿越森林的路径是循环性的,依赖于资源,同一地点会在个体的一生中被反复占用。因此,森林对他们来说是一系列邻里,在某些方面是野生的、潜在危险的,但通过世代人类的存在和互动,从根本上被驯化了。景观的每一个特征都回响着一个故事。小径上的每一点,每一块巨石和洞穴,流经他们土地的两千多条溪流中的每一条都有名字。管理意识渗透到本南社会中,始终如一地指导着人们利用和分配环境的方式。个人资源——一丛西米棕榈、果树、毒箭树、捕鱼地点、药用植物——都归属于个别亲属群体,这些家族权利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并世代传承。“从森林中,”他们非常简单地说,“我们得到生命。”
1989年我第一次拜访本南人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存在的品质,一种根本的人性,这种人性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结果。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概念,除了自然界的节律——植物的结果季节、日月的运行、黄昏前两小时出现的汗蜂、每晚六点准时让森林充满电力的黑蝉。他们没有带薪工作的概念,没有工作作为负担、休闲作为娱乐的对立观念。对他们来说,只有生活,日常的循环。孩子们不是在学校学习,而是通过经验学习,经常在父母身边。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常分散很远,自给自足是常态,每个人都能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务。所以几乎没有等级观念。
在一个没有专家的社会中,在每个人都能用森林中随处可得的原材料制作一切物品的社会中,在一个没有积累物质财富动机的社会中(因为一切都必须背在身上),你如何衡量财富?本南人明确地将财富视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力量,因为如果这些关系削弱或破裂,所有人都会受苦。如果冲突导致分裂,家庭长期分道扬镳,两个群体都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猎手而挨饿。因此,如同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一样,直接批评他人是不被赞成的。优先考虑的总是群体的团结。冲突和愤怒的表现极其罕见。文明和幽默是常态。
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谢谢”这个词,因为分享是一种义务。没人知道下一个带食物到火边的会是谁。我曾经给一位老妇人一支香烟,看着她把它撕开,将各股烟丝公平地分配给营地的每个庇护所,虽然这使产品变得无用,但她履行了分享的义务。在我第一次访问后的一段时间,一些本南人来到加拿大为保护他们的森林而奔走,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无家可归现象。他们无法理解在温哥华这样富裕的地方怎么会存在这样的事情。加拿大人或美国人从小相信无家可归是生活中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特征。本南人遵循这样的格言:穷人让我们所有人蒙羞。确实,在他们文化中最严重的过错是sihun,这个概念本质上意味着分享的失败。
本南人缺乏文字;在任何时候,语言的总词汇量始终是最好的讲故事者的知识。这也产生了后果。写作虽然明显是人类历史上的非凡创新,但从定义上讲是一种出色的速记,它允许甚至鼓励记忆的麻木。口传传统锐化回忆,甚至似乎与自然界开启某种神秘的对话。正如我们读小说时能听到角色的声音,本南人感知森林中动物的声音。每一个森林声音都是精神语言的要素。当树木听到裸喉鸟优美的歌声时会开花。从某个方向听到的鸟鸣带来好消息;从不同方向听到的相同声音可能是不祥的预兆。整个狩猎队伍可能会因为条纹翠鸟的叫声、蝠鹰的啼叫而返回营地。其他鸟类,如蛛猎鸟,引导本南人找到猎物。在开始长途旅行之前,他们必须看到白头鹰并听到冠雨鸟的叫声和吠鹿狗一样的声音。
这段非凡的对话以很少有外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影响着本南人的生活。但有一个人理解了,他就是布鲁诺·曼瑟(Bruno Manser),一位瑞士活动家,曾与本南人共同生活了六年,后来又回到了他们的家园,并在那里死于神秘的环境中。“每天黎明时分,”布鲁诺写道,“长臂猿的嚎叫声传播很远,借助森林的凉爽和太阳照射树冠时上方温暖空气所形成的热边界传播。本南人从不吃长臂猿的眼睛。他们害怕在地平线中迷失自己。他们缺乏内在的地平线。他们不把梦境与现实分开。如果有人梦见树枝落在营地上,他们会在黎明时搬走。”
可悲的是,到布鲁诺于2000年失踪、命运不明时,森林的声音已经变成了机械的声音。整个1980年代,当亚马逊雨林的困境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时,巴西的热带木材出口量不到3%。马来西亚占产量的近60%,其中大部分来自砂拉越(Sarawak)和本南人的家园。婆罗洲北海岸的商业木材采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而且规模很小。到1971年,砂拉越每年出口420万立方米的木材,其中大部分来自内陆的高原森林。1990年,年砍伐量已升级到1880万立方米。1993年,当我第二次回访本南人时,仅在巴拉姆河(Baram River)流域就有三十家伐木公司在作业,其中一些配备了多达一千二百台推土机,在超过一百万英亩传统上属于本南人及其近邻的森林土地上工作。本南人土地的70%被政府正式指定为伐木区。非法作业威胁着其余的大部分地区。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本南人的世界被颠覆了。在森林中长大的妇女发现自己在伐木营中做仆人或妓女,这些营地用废料和淤泥污染了河流,使捕鱼变得不可能。在政府安置营中从未患过文明疾病的儿童死于麻疹和流感。本南人选择了抵抗,用藤条路障封锁伐木道路。这是一个勇敢但不切实际的姿态,吹管对抗推土机,最终无法抵挡马来西亚国家的力量。
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的政策是,”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ad)指出,“最终将所有丛林居民带入主流社会。这些无助的、半饥饿的、疾病缠身的人没有什么浪漫可言。”时任砂拉越住房和公共卫生部长的詹姆斯·王(James Wong)补充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像动物一样到处乱跑。没有人有道德权利剥夺本南人融入马来西亚社会的权利。”
这就是政府立场的本质。游牧民族是民族国家的尴尬。为了将本南人从落后中解放出来,政府必须将他们从真实的自己中解放出来。像本南人这样的原住民被认为阻碍了发展,这成为剥夺他们财产和摧毁他们生活方式的理由。然后他们的消失被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古老的民族不能指望在二十一世纪生存。
“否认他们现代世界的进步是对的吗?”恼怒的马来西亚初级商品部长林敬益(Lim Keng Yaik)问道。“让他们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住两年,享受凯迪拉克、空调和每天餐桌上美味多汁牛排的便利设施。然后当他们回来时,让他们选择是要像纽约人那样生活,还是作为热带雨林中的天然本南人生活。”
1992年,一个本南人代表团确实前往了纽约,虽然据我回忆,他们没有住在华尔道夫酒店。12月10日,安德森·穆唐·乌鲁德(Anderson Mutang Urud)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政府,”他开始说道,“说它正在给我们带来发展。但我们看到的唯一发展就是尘土飞扬的伐木道路和搬迁营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所谓的进步只意味着饥饿、依赖、无助、我们文化的破坏和我们人民的士气消沉。政府说它在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工作。我们为什么需要工作?我的父亲和祖父不必向政府要工作。他们从不失业。他们靠土地和森林生活。那是美好的生活。我们从不饥饿或匮乏。这些伐木工作会随着森林一起消失。十年内所有的工作都会消失,维持我们数千年的森林也会随之消失。”
就在1960年,我出生后七年,绝大多数本南人还过着游牧生活。当我1998年第三次回访时,也许还有一百个家庭完全生活在森林中。就在一年前,我收到了伊恩·麦肯齐(Ian Mackenzie)的一张便条,他是一位将学术生涯献给本南语研究的加拿大语言学家。伊恩证实,最后的家庭也已经定居了。世界上最非凡的游牧文化之一的生存基础已被摧毁。在本南人的传统家园中,西米和藤条、棕榈、藤本植物和果树都压在森林地面上。犀鸟与野鸡一起逃走了,随着树木继续倒下,一种在道德上受到启发、本质上正确、几个世纪以来毫不费力地延续的独特生活方式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崩溃了。
当我第一次参观柬埔寨的高棉寺庙吴哥窟时,我遇到了一位年长的佛教尼姑,她的手脚在波尔布特和杀戮场时代被从身体上砍掉。她的罪名是她的信仰,她的惩罚是一个政权和意识形态的野蛮回应,这种意识形态否认精神信仰的所有细微差别,甚至否认民族性和文化的概念本身。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和意识的无限排列组合简化为所有者和工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简单对立,它由一位德国哲学家在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创立,在某种意义上是笛卡尔启发的机械存在观的完美胜利。社会本身就是一台可以为所有人的福祉而设计的机器。这正是波尔布特,一号兄弟,心中所想的。他认为自己在帮助,推动历史前进,即使这意味着300万人的死亡。数十个国家的革命干部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欧洲理念——强加给像西伯利亚的涅涅茨驯鹿牧民、生活在马里悬崖祖先墓穴下的多贡人、成吉思汗的蒙古后裔、老挝人和越南人、班图人、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等如此多样的民族,如果不是其后果对人类大部分地区如此灾难性,这种尝试看起来几乎是可笑的天真。“任何认为只有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彼得·马蒂森曾写道,“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他心中无疑想的是波尔布特、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这样的人。
在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血腥的暴力世纪”中,毛泽东承担着在杀害自己人民方面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这一黑暗荣誉。当毛泽东著名地在年轻达赖喇嘛耳边低语说所有宗教都是毒药时,这位西藏精神领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大跃进,一个极其错误构思的集体化所有生产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的运动,在1959年导致40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同年,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完全意图摧毁西藏佛教传统。
意识形态狂热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控制和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其目标是创造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干部队伍,这些男男女女的思想已经被清洗,记忆被抹除,以产生一个模板,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被刻在上面。真正公正的社会将在破四旧的废墟中出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旧立新。这是被宣传为社会主义天堂到来前最后一战的官方口号。
所有关于宗教和精神的概念、文化和家庭的诗意、关于男女与自然关系的直觉、土壤的芳香以及雨滴落在石头上的意义,在毛泽东的转化和统治算计中都没有位置。民族性被认为仅仅是经济差距的产物。一旦物质不平等得到解决,民族差异就会消失。当然,西藏代表旧的;中国,代表新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既暗示又要求对西藏古老文明的每个方面进行全面攻击。超过一百万藏人被杀害,最终6000座寺院和庙宇、佛塔和宗教圣地被夷为平地,被来自空中和地面的大炮和炸弹炸毁。想象一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家,如果一个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国家入侵,宣布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可憎的,并继续摧毁我们所有的教堂、犹太会堂、寺庙和清真寺,我们作为加拿大人会有什么感受。我强调问题不在于中国人民,他们在毛泽东统治下遭受的痛苦超过任何人。疯狂的产生是因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源于另一层暴力,一种由殖民历史和混乱文化接触的意外且无法控制的结果所产生的压力。
几年前,当我与两位朋友马修·里卡德(Matthieu Ricard)和谢拉布·巴玛(Sherab Barma)在喜马拉雅山旅行时,这段历史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马修是一位有灵感的作家和摄影师,他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分子生物学的高级研究生学习,然后在大约四十年前离开学术界,发誓成为一名西藏僧侣。十多年来,他是宁玛传统受人尊敬的精神喇嘛钦哲仁波切的学生和私人助手,今天从他在加德满都谢钦寺的基地,马修仍然是达赖喇嘛尊者的知己和翻译。谢拉布是一位传统的西藏医生,他的七年训练包括在洞穴中进行为期十二个月的独自静修,他每年都会回到那里进行一个月的冥想。我们三人在奇旺会面,这是一座美丽的寺院,像燕子窝一样依附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的山腰上。从那里我们去了图登曲林圣地,这里是大约800名僧侣和尼姑的家园,他们将生命奉献给个人转化和马修所说的”西藏佛教的心智科学”。这个短语的使用让我很感兴趣,特别是因为马修在他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曾追求科学研究职业,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的实验室工作过。
“什么是科学,”他一天早上说道,“无非是对真理的经验主义追求?什么是Buddhism,无非是对心性本质进行了2500年的直接观察?一位喇嘛曾经告诉我,西方科学和效率为次要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试图活到一百岁而不掉头发或牙齿。Buddhism徒用一生的时间试图理解存在的本质。欧洲城市的广告牌上展示着穿内衣的青少年。西藏的广告牌是mani墙,雕刻在石头上的咒语,为一切有情众生的福祉而祈祷。”
Matthieu解释说,Buddhism道路的精髓浓缩在四谛(Four Noble Truths)中。一切生命都是苦。Buddha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一切生命都是否定,而只是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邪恶不是例外,而是现存事物秩序的一部分,是人类行为或业力(karma)的结果。痛苦的原因是无明。Buddha所说的无明不是指愚蠢。他指的是人类倾向于执着于自己永恒性和中心性的残酷幻象,执着于他们与普遍存在之流的孤立和分离。第三谛的启示是无明可以被克服,第四谛也是最重要的一谛是对一种观照实践的描述,如果遵循这种实践,就承诺能够结束痛苦,实现人心的真正解脱和转化。目标不是逃离这个世界,而是逃离被世界奴役。实践的目的不是消除自我,而是消灭无明,揭示真正的Buddha本性,它像埋藏的宝石一样在每个人内心闪闪发光,等待被发现。简而言之,Buddha的传承提供的不亚于一张通往开悟的路线图。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Matthieu和Sherab带领我进行了一次非凡的朝圣,最终我们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侧翼。我们的目标不是这座山,而是一位名叫Tsetsam Ani的简朴Buddhism尼姑的家。Sherab解释说,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她曾经非常美丽,但专心于dharma,对婚姻毫无兴趣。尽管如此,一位有权要求她家族订婚的富商仍在追求她,她通过爬下悬崖边的茅厕逃脱,最终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在那里她出家受戒。当她回到尼泊尔昆布谷的家时,她开始了终身闭关。四十五年来,她没有离开过一个小房间的范围。她有一些人际接触。每天有人送食物,现在她年老了,Sherab作为医生时常检查她的身体。但她基本上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观照实践和独处。她是英雄中的英雄,真正的菩萨(Bodhisattva),智慧英雄,已找到开悟但仍留在samsara领域——痛苦和无明的领域——帮助一切有情众生实现自己解脱的觉悟存在。
走近她小房间的百叶窗,我以为会遇到一个疯女人。相反,木门打开后露出了最快乐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和笑声。她的头发夹杂着灰色,剪得很短。她的身体纤细但强壮,只有当她双手合十行礼时,我才意识到她确实有多老。她给我们提供糖果,然后立即因为寺院生活中复杂、巴洛克式和完全不必要的仪式而责备Matthieu。她已经将自己的整个宗教实践精炼为一个咒语,Om Mani Padme Hum,六个音节代表在整个samsara被清空并通过Buddha的心要拥抱完全纯净之前必须通过的六道。在四十五年里每个清醒时刻都念诵这一祷告,她将自己奉献给慈悲和慈爱的传播。每一次呼吸她都更接近她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境,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条救赎和解脱的道路。
我们与Tsetsam Ani待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让她继续她的修行。当我们离开村庄时,恰好遇到一些登山者正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做这位温和女子所做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会称之为浪费人生。大多数西藏Buddhism徒同样觉得选择走到空气稀薄到意识被湮灭的高度是令人费解的。故意进入死亡地带,冒险失去个人转化和逃离samsara领域的机会,仅仅为了爬一座山,对他们来说是愚人的愚行,是对珍贵化身的真正浪费。
Buddhism徒花时间为我们大多数人用一生时间假装不存在的时刻做准备,那就是死亡。我们生活在活动的旋涡中,与时间赛跑,用物质世界的标准来定义成功,财富和成就,各种各样的资历。对Buddhism徒来说,这就是无明的本质。他们提醒我们,一切生命都会老去,一切财产都会腐朽。每一刻都是珍贵的,我们都有选择,继续在妄想的旋转木马上,还是踏入精神可能性的新领域。他们提供的选择不是教条而是道路,漫长而艰难,但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可抗拒的。
佛教徒不谈论罪恶与审判,不讨论善恶,而只关注无明与痛苦,所有重点都在于慈悲。皈依佛陀不需要盲目信仰的行为,当然也不意味着有义务去说服世界其他人按你的想法思考。在其核心,它只是一种智慧哲学,一套禅修实践,一条由2500年经验观察和推理所指引的精神道路,如果遵循,必定承诺人心的转化。通过佛法获得宁静是验证佛教心理学的实验证明,就像落苹果向我们证明重力的存在一样。理解这一切的含义可能很困难,但它对藏人来说确实存在。许多藏人不相信我们登上了月球,但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可能不相信他们在此生获得开悟,但他们确实做到了。
在《金刚经》中,佛陀告诫世界是短暂的,如风中之烛,如幻影,如梦境,如黎明中消逝的星光。正是基于这种洞察,藏人衡量他们的过去并规划他们的未来。他们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去问,我们怎么可能允许如此巨大的悲伤席卷他们的土地,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容忍中国的愤怒,即使它继续追求拆除藏族文化和违背一个真正为人类贡献良多的民族和国家。
正如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一直残酷而复杂,这根本上是一个关于权力和傲慢的故事,一个民族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个民族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以及这种强加所暗示的知识和文化优越性的主张。这种基本动态也推动着作为现代发展范式的进步崇拜。动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加仁慈,尽管中国政府确实坚信其在西藏政策的正义性,但对于那些国际社会选择改变和改善其生活的民族和文化来说,后果可能同样具有毁灭性。
在肯尼亚北部的Kaisut沙漠中,干旱不是残酷的异常现象,而是气候的常规特征。在干旱中生存是所有游牧民族的关键适应要务,这些部落民族如Rendille、Samburu、Ariaal、Boran和Gabra。为了保证氏族的延续,维持足够大的骆驼和牛群至关重要,这样至少一些动物能够在极端干旱期间存活,并提供重建家庭财富的基本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责任和义务决定了社会的结构;它造就了人们的本质。为了维持大型畜群,族长拥有大量子女是有益的,因此这些社会通常是一夫多妻制。但随着男性娶多位妻子,就面临着如何处理那些可能没有伴侣结婚的精力充沛的适婚年龄年轻男子的挑战。长者们基本上通过摆脱年轻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派遣他们到偏远的营地度过十年时间,在那里他们承担保护畜群免受敌人掠夺者侵害的职责。为了让这种与社区社会空间的分离变得令人向往,它被赋予了威望。年轻男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一个他训练数月的仪式,就是他的公开割礼,这是他进入战士特权世界的时刻。仪式每十四年只举行一次,那些一起忍受仪式的人终生结为兄弟。如果一个小伙子在包皮上划九道切口时退缩,他将永远羞辱他的氏族。但很少有人失败,因为荣誉是巨大的。
在身体、社会和精神上都得到转化后,战士们迁移到沙漠,在那里他们共同生活,以在脆弱金合欢树荫下采集的草药为食,混合每晚从母牛颈静脉抽取的牛奶和血液。然而,仍然存在人类性欲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战士们被允许定期回到社区,前提是他们不能接近已婚妇女。然而,他们被允许接近未婚少女。婚前性关系是公开和被容忍的,直到年轻女子被许配给长者的那一刻,此时关系必须终止。但战士被鼓励并且确实被期望参加他前情人的婚礼,并公开嘲笑取代他在情人身边位置的老人的男性气概。一个单一的适应性挑战,在干旱中生存,在整个文化中产生共鸣,为这些游牧部落定义了作为人类的意义。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一系列灾难性干旱,加上邻近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种族冲突和战争引起的饥荒,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凯苏特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邻近地区的关注。发展组织认为,萨赫勒地区的退化和人民的贫困是过度放牧的后果,在学术语言中被称为”公地悲剧”。只要人们不拥有土地,个人贪婪就会不可避免地战胜社区利益。解决方案是私有化,并从美国西部整体引入土地管理计划。1976年,联合国启动了一项数百万美元的倡议,鼓励部落定居并进入现金经济,通过出售牲畜来减少他们的畜群规模。这种外部处方,呼应了英国殖民地自1920年代以来将部落转变为定居生活的努力,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数百年来,游牧民族的生存本身就依赖于他们对土地的照料。沙漠就是他们的家园。使用动物将草类和灌木植被转化为蛋白质是对土地最有效的利用,也是在沙漠中生活的唯一方式。调解这一过程,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和福祉与集体命运的关系,是复杂的血缘关系,这些关系过于微妙,外人难以轻易察觉。游牧民族的天才正是他们在沙漠中生存的能力。
当天生就要迁移的人们被迫定居下来时,问题就开始了。水洞发展成救济营地,这些营地又逐渐发展成小城镇,都成为依赖的绿洲。那些出售动物的人成为国际援助机构的受监护人,这些机构分发玉米,主要是爱荷华玉米,必须煮熟才能食用,因此最后的树木被砍伐来制作木炭。那些有幸有能力的人派遣他们的长子到传教站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进入了教会的影响范围。
1998年我穿越凯苏特时,我访问了科尔的一个传教站,一个难民定居点,遇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乔治神父,一位意大利牧师,他在1975年建立了食物救济行动。当时科尔只是一个季节性营地,是小群游牧伦迪勒牧民访问的水源。当我到达那里时,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有16,000人口,170口手挖井,2,500座房屋,所有房屋都用硬纸板、麻布和印有国际援助组织名称的金属板作屋顶。乔治神父是他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教育,”他告诉我,“并没有让人们变得更好。这是我心中的痛苦。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不想与他们的动物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想离开。教育不应该成为离开的理由。这是回来的义务。”
问题是很少有人这样做。正如乔治神父承认的那样,他们获得了一点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某些基本技能,但在一种教学法和氛围中,这种教学法教会他们蔑视自己的父亲和传统。他们作为游牧民族进入学校,作为办事员毕业,然后南漂到城市,那里官方失业率为25%,超过一半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工作。夹在两个世界之间,无法回去,也没有明确的前进道路,他们在内罗毕的街头谋生,增加了围绕肯尼亚首都的苦难之海。
“他们必须坚持传统,”乔治神父告诉我。“最终这就是拯救他们的东西。这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是伦迪勒人,必须保持伦迪勒人的身份。”
在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去世前,她谈到了她独特的恐惧:当我们朝着一个更加同质化的世界漂移时,我们正在奠定一种乏味、无定形、独特通用的现代文化的基础,这种文化将没有竞争对手。她担心,人类的整个想象力可能被限制在单一智力和精神模式的范围内。她的噩梦是我们可能某天醒来时甚至不记得失去了什么。我们这个物种已经存在了大约20万年。新石器革命给了我们农业,随之而来的是盈余、等级制度、专业化和定居生活,这只发生在一万到一万两千年前。我们所知的现代工业社会只有300年的历史。这种浅薄的历史不应该暗示我们中的任何人,我们对未来千年中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将面临的所有挑战都有所有答案。目标不是让人们冻结在时间中。人们无法把雨林公园化。文化不是博物馆藏品;它们是有真实需求的真实人群的社区。正如休·布罗迪所写,问题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自由民族选择其生活组成部分的权利。重点不是拒绝接触,而是确保所有民族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从现代性的天才中受益,而不需要这种参与要求他们民族身份的死亡。
当我们使用现代性或现代世界这个术语时,反思我们的意思可能是有用的。所有文化都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对自己的现实解释极其忠诚。实际上,许多土著社会的名称翻译为”人民”,暗示其他每个人都是非人类,是来自文明领域之外的野蛮人。barbarian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barbarus,意思是胡言乱语的人。在古代世界,如果你不说希腊语,你就是野蛮人。阿兹特克人也有同样的观念。任何不能说纳瓦特尔语的人都是非人类。
我们也在文化上目光短浅,经常忘记我们所代表的不是历史的绝对潮流,而仅仅是一种世界观,而现代性——无论你将其定义为西方化, 全球化, 资本主义, 民主制, 还是 自由贸易 ——都只是我们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它并不是某种脱离文化约束的客观力量。它当然也不是历史真正且唯一的脉动。它仅仅是一系列信念、信仰、经济范式的组合,代表着做事的一种方式,代表着组织人类活动这一复杂过程的一种方法。毫无疑问,我们的成就令人震惊,我们的技术创新令人眼花缭乱。仅仅是上个世纪现代科学医学体系的发展就代表了人类努力中最伟大的篇章之一。如果你在车祸中断了肢体,你肯定不会想被送到草药医生那里。
但这些成就并不能使西方范式变得特殊,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表明它已经或应该垄断通往未来的道路。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人类学家降落在美国会看到许多奇妙的事物。但他或她或它也会遇到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崇尚婚姻,却允许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钦佩老人,却只有6%的家庭中祖父母与孙辈同住;热爱孩子,却拥抱一个口号——“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这意味着完全献身于工作而牺牲家庭。到十八岁时,美国青年平均花费两年时间看电视。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临床肥胖,60%的人超重,部分原因是20%的餐食在汽车中消费,三分之一的儿童每天吃快餐。这个国家每年制造2亿吨工业化学品,而其人民消费了世界三分之二的抗抑郁药物产量。四百个最富有的美国人控制的财富超过了与他们共享地球的最贫穷的八十一个国家的25亿人口。这个国家在军备和战争上的支出超过了其十七个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的军事预算总和。加利福尼亚州在监狱上的支出超过了在大学上的支出。技术奇迹与拥抱一种危害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生产和消费经济模式相平衡。极端 是对一个文明的恰当形容词,这个文明用其废料污染空气、水和土壤;使植物和动物灭绝的规模自恐龙消失以来在地球上前所未见;筑坝截流,砍伐古老森林,清空海洋中的鱼类,却很少抑制威胁改变大气化学和物理性质的工业过程。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令人钦佩,但并不是人类潜能的典范。一旦我们通过人类学的透镜观察,或许第一次看到所有文化都有反映几代人选择的独特属性,就会变得绝对清楚:人类的生活和命运中不存在普遍的进步。如果社会要根据技术实力来排名,西方科学实验,光辉而灿烂,无疑会名列前茅。但如果优秀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例如以真正可持续的方式繁荣的能力,以及对地球真正的敬畏和欣赏,那么西方范式就会失败。如果推动我们物种最高抱负的动力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直觉的范围、承认宗教渴望多样性的哲学慷慨,那么我们教条式的结论将再次被发现不足。
当我们将现代性,正如我们定义的那样,投射为所有人类社会的必然命运时,我们正在极度虚伪。事实上,西方发展模式在许多地方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基于一个虚假的承诺:遵循其规定指令的人们最终将获得少数西方国家享有的物质繁荣。即使这是可能的,也完全不清楚这是否可取。根据当前的人口预测,要将世界各地的能源和材料消费提高到西方水平,到2100年将需要四个地球的资源。在我们拥有的这一个世界中做到这一点,将意味着如此严重地危害生物圈,以至于地球将面目全非。考虑到驱动国际社会大多数决策的价值观,这是不会发生的。实际上,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发展一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被从过去中撕裂,被推向不确定的未来,只是为了在一个通往nowhere的经济阶梯的最底层获得一个位置。
考虑发展范式的关键指标。预期寿命的增长暗示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但这并不能说明那些存活到童年之后的人们所过生活的质量如何。全球化被以标志性的强度来庆祝。但它真正意味着什么?在孟加拉国,服装工人拿着微薄的工资缝制衣服,这些衣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零售价格是几十美元。在美国销售的玩具和体育用品中,80%是在中国的血汗工厂生产的,那里数百万人的工资低至每小时12美分,每年有40万人因空气污染过早死亡,4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河流被工业毒素严重污染。《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巴基斯坦拉合尔,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赛义德的人在一家为Gap和Eddie Bauer供货的工厂缝制衬衫和牛仔裤,月收入88美元。他和五名家庭成员共用一张床,住在一个房间的家中,这个家隐藏在满是污水和垃圾的小巷迷宫中。他的收入是上一份工作的三倍,他就是全球化的典型代表。
毫无疑问,舒适和财富的形象,技术先进的形象,具有磁性的吸引力。城市里的任何工作似乎都比在烈日炙烤的田野里从事背负重担的劳动要好。被新事物的承诺所迷惑,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自愿且非常认真地背离了传统。正如我们在肯尼亚所看到的,后果可能会令人深感失望。绝大多数切断与传统联系的人的命运不是获得西方的繁荣,而是加入城市贫民的大军,被困在肮脏的环境中,努力求生存。随着文化的凋零,个人依然存在,往往只是他们昔日自己的影子,被困在时间中,无法回到过去,却被剥夺了在一个世界中获得真正地位的任何可能性,而他们寻求模仿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渴望获得这个世界的财富。这创造了一种危险和爆炸性的局面,这正是为什么不同文化的困境不仅仅是怀旧的简单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人权问题,而是地缘政治稳定和生存的严重问题。
如果让我从这些马西讲座中提炼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文化并非微不足道。它不是装饰或人工制品,不是我们唱的歌曲,甚至不是我们吟唱的祷告。它是一条给生活带来意义的舒适毯子。它是一套知识体系,允许个人从意识的无限感觉中找出意义,在一个最终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秩序的宇宙中找到意义和秩序。文化是一套法律和传统体系,一套道德和伦理准则,它将一个民族与野蛮之心隔离开来,历史表明这种野蛮之心就潜伏在所有人类社会甚至所有人类的表面之下。只有文化才能让我们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触及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
如果你想知道当文化和文明的约束丧失时会发生什么,只需环顾世界,考虑上个世纪的历史。人类学表明,当人民和文化受到挤压时,往往会出现极端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受到奇异和意想不到的信念的启发。这些”复兴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s),一个可怕且误导性的学术术语,可能是良性的。在牙买加,300年的殖民主义加上独立后的经济萧条,使得许多年轻人来到Trenchtown的棚户区,在可能过量的大麻影响下,拉斯塔法里教徒将海尔·塞拉西,一个非洲小暴君,视为犹大的雄狮。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观念,但最终是无害的。
更典型的是,这样的运动对其追随者和他们所对抗的人都是致命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不仅仅寻求结束鸦片贸易或驱逐外国人。义和团的兴起是对一个古老民族屈辱的回应,这个民族长期以来一直是已知世界的中心,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被门外的未知野蛮人降为奴隶。仅仅杀死传教士是不够的。在一个原始的、返祖的姿态中,他们的身体被肢解,头颅被挂在长矛上展示。
在柬埔寨,波尔布特在国内受到法国人的羞辱,在巴黎留学时在国外受到羞辱,他创造了一个重新焕发的高棉帝国的幻想,一个清除了所有西方事物的国家,除了为谋杀提供理由的基本意识形态。因此,虽然12世纪的吴哥大寺庙在内战期间免于被毁,但所有戴眼镜的人或有学者、诗人、商人和牧师柔软双手的人都在杀戮场被清算。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系统性强奸今天被编成恐怖武器,这是唯一连贯的战争策略,而在乌干达,孤儿青年组成的民兵以基督的名义劫掠和掠夺。在利比里亚,吸毒后赤身裸体的儿童作为光屁股营(Butt Naked Battalion)参加战斗,这是一个由弥赛亚式军阀约书亚·米尔顿·布拉希(Joshua Milton Blahyi)领导的邪教组织,他说服他们相信他的撒旦力量会让他们无敌。在十四年的内战中,他们谋杀、强奸和吃掉了数千人。随着和平的到来,被称为光屁股将军的布拉希重新塑造自己为福音传道者,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街头寻找皈依者和救赎,他今天仍生活在那里。
在尼泊尔,农村农民高声宣扬着自斯大林去世以来未曾听到的言辞。在秘鲁,光辉道路转向了毛主义。如果他们转而援引十八世纪土著反叛者、印加族后裔图帕克·阿马鲁,如果他们能够抑制对他们声称要代表的土著人民的本能蔑视,他们很可能如其所愿地让国家陷入火海。利马这座1940年拥有40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居住着900万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阳光炙烤沙漠中的贫困之海。
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基地组织追随者援引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封建过去,以合理化他们自身的屈辱和仇恨。他们是伊斯兰文化中的癌症,既不完全属于这个信仰,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像任何恶性肿瘤一样,他们必须从肌体中切除并摧毁。同时,我们必须努力理解这个以及其他此类运动的根源,因为被剥夺公民权的混乱状况存在于世界各地心怀不满的人群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有60个民族国家。今天有190个,其中大多数都贫穷且极不稳定。真正的故事发生在城市中。在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及其所有承诺,已将数百万人吸引到肮脏之中。墨西哥城和圣保罗的人口数量未知,可能无法计量。在亚洲,有些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我们西方人大多数都叫不出名字。在未来二十年里,世界人口将从60亿增长到80亿,而这一增长的97%将发生在平均个人收入不足每天2美元的国家。
正如哈佛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写,民族国家对于世界的大问题来说太小了,对于世界的小问题来说又太大了。在主要工业国之外,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融合与和谐,而是带来了一场变革的风暴,这场风暴席卷了语言和文化、古老技能和远见卓识。
这不必发生。承认其他文化的奇迹并不是贬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以某种谦逊认识到其他民族,尽管他们也可能有缺陷,但仍然为我们的集体遗产——人类思想、信仰和适应性的全套资源——做出了贡献,这些资源历史上使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得以繁荣。理解这个真理就是本能地感受到语言消失或民族同化所固有的悲剧。失去一种文化就是失去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整日击打森林的雨终于停了。阿西克杀死的鹿头在我们脚边的煤炭中烤着。云层散开,透过树冠的枝叶,满月的光芒突然照亮了我们的营地。阿西克抬头看着月亮,随意地问是否真的有人去过那里,只是带着装满石头的篮子回来。如果他们只找到了这些,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呢?花了多长时间,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对一个用燧石生火的人来说,很难解释一个消耗了各国财富、耗资近万亿美元将十二个人送上月球的太空计划。或者说他们在太空中航行了数十亿英里后,确实只带回了岩石和月尘,总共828磅。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西克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进入太空不是为了获取财富。我们去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很好奇,我们带回的不是宝藏,而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对生命本身的新视野。关键时刻出现在1968年圣诞夜,当阿波罗8号从月球背面出现时,看到在月球表面升起一个小而脆弱的星球,漂浮在太空的天鹅绒虚空中。不是日出,也不是月亮的阴影,而是地球本身在升起。这个图像比任何数量的科学数据都更能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有限的地方,一个由生命构成的单一互动球体,一个由空气、水、风和土壤组成的生命有机体。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医生斯托里·马斯格雷夫曾告诉我,体验到那种景象——一种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辉煌才能看到的景象——然后回忆起我们对待我们唯一家园的冷漠和无意识的方式,就是体验到最纯粹的恐惧感。但他补充说,也有新开始的兴奋和期待,因为各民族和国家必须改变他们的方式。
他们确实改变了。仅仅四十年前,让人们停止从车窗向外扔垃圾就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环保胜利。雷切尔·卡森是荒野中的孤独声音。仅仅十年前,警告全球变暖严重性的科学家们还被斥为激进分子。今天,质疑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人才占据了疯狂的边缘。当我还是研究生时,生物圈(biosphere)和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奇异的术语,只有少数科学家熟悉。今天它们已经成为学童词汇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危机——仅在过去三十年中就有超过一百万种生命形式灭绝——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主要环境挑战的解决方案可能仍然难以捉摸,但地球上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忽视威胁的严重性或困境的紧迫性。这代表了人类优先事项的重新定位,在其意义上具有历史性,在其前景上具有深刻的希望。
类似的转变正在发生,而且来得正是时候,这种转变体现在人们看待和评价文化的方式上。在很多方面,加拿大都在引领潮流,不仅作为一个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的典范,而且作为一个愿意承认过去错误并寻求适当补救措施的民族国家,即使在它规划作为多元社会的前进道路时也是如此。每当我在北极地区旅行时,我都会想起这一点,特别是去努纳武特,这个新的领土,一个大约相当于西欧大小的家园,现在由26,000名因纽特人进行行政管理。除了哥伦比亚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哪个民族国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努纳武特的存在本身就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强有力的声明,表明加拿大认识到独特的族群、土著民族、原住民并不会阻碍国家的命运;相反,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会为国家的命运做出贡献。他们的文化生存不会削弱民族国家;如果国家愿意拥抱多样性,文化生存就会丰富民族国家。这些文化不代表现代性的失败尝试,不是那些以某种方式错过了历史技术列车的边缘民族。相反,这些民族,带着他们的梦想和祈祷,他们的神话和记忆,告诉我们确实存在其他的存在方式,关于生活、出生、死亡和创造本身的另类愿景。当一个民族国家准备承认这一点时,那么世界所有民族确实都有希望了。
当你考虑到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在重新定义这种关系方面已经走了多远时,这个想法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特别是对因纽特人来说,最初的文化冲突是极其创伤性的。当英国人首次到达北极时,他们认为因纽特人是野蛮人;因纽特人认为英国人是神。两者都错了,但有一方更能彰显人类的荣耀。英国人未能理解,没有比能够在北极环境中生存更好的天才标准了,而且使用的技术仅限于你能从象牙和骨头、鹿角、皂石和石板中雕刻出来的东西。雪橇的滑板最初是用鱼制成的,三条北极比目鱼排成一排,用驯鹿皮包裹并冻结。因纽特人不害怕寒冷,他们利用寒冷。
模仿他们方式的欧洲探险队取得了伟大的探索成就。那些没有这样做的探险队则遭受了可怕的死亡。当富兰克林勋爵的手下在阿德莱德半岛的饥饿湾被发现冻死时,年轻的水手们在一架重达650磅的铁橡木雪橇的皮革牵引带中僵硬地死去。雪橇上装着一艘800磅重的小船,船上装满了英国海军军官的所有个人物品,包括银餐具,甚至还有一本小说《韦克菲尔德牧师》。他们以某种方式期望能够拖着这些东西穿过冰面,穿越北方广袤的北方森林,都怀着遇到另一艘船或者哈德逊湾公司前哨站的希望。
相比之下,因纽特人在大地上轻装而行。我曾经和来自北极湾的几个家庭在巴芬岛顶端的克劳福德角的狩猎营地度过了几天。每年夏天六月,在地球上最史诗般的动物迁徙之一中,1700万海洋哺乳动物返回北极,穿过兰开斯特海峡的开阔水域。将巴芬岛北岸一分为二的海军上将湾仍然被冰封锁,猎人们沿着浮冰边缘行进,那里是冰与海相接的地方,聆听着鲸鱼的呼吸与风声交融。有一天,或者也许是夜晚,因为六月的太阳永不落,奥拉尤克·纳尔齐塔尔维克告诉我一个非凡的故事。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是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加拿大政府为了在北极建立主权,基本上强迫因纽特人进入定居点,在某些情况下将整个人口从他们的家园迁移数百公里。有一个老人拒绝离开。担心他的生命安全,他的家人拿走了他所有的工具和武器,认为这会迫使他离开这片土地。然而,在暴风雪中,他走出他们的冰屋,排便,并将粪便磨成冰冻的刀刃,用唾液的喷洒将其磨锋利。用这把由寒冷从人类排泄物锻造的刀,他杀死了一只狗。用狗的胸骨当雪橇,用狗皮套住另一只狗,他消失在黑暗中。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的,尽管我确实在丹麦探险家彼得·弗罗伊申的北极日记中找到了对这种工具的提及。但无论真假,它都是因纽特人智慧和韧性的绝佳象征,这些文化特质使他们得以生存。
在最近一次北极之旅中,当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安迪·格雷格和我与西奥·伊库马克、约翰·阿纳齐亚克以及来自伊格卢利克的一队猎人一起出发到海冰上寻找北极熊时,我又想起了这个故事。我们在离岸大约150公里的地方旅行,加上风寒,温度在零下50摄氏度左右徘徊。一辆拖着满载kamotik的雪地摩托撞上了一块流浪的冰块,失去控制打转,雪橇的惯性使它越过了驾驶员和机器。其中一根滑雪板扭得像椒盐脆饼干,另一根完全断成两半。我惊讶地看着西奥和约翰敲打金属,用步枪近距离射出四个洞,用一块废铁即兴制作夹子,从曲棍球棒上找到夹板,在二十分钟内把整个装置重新绑在一起。我们继续推进到夜晚,直到几天后,那个驾驶员才随口提到在事故中他摔断了脚。
Theo和John一起长大,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概括了二十世纪因纽特人的故事。今天的Igloolik是努纳武特的文化中心,历史上与外界的接触极少。1821-22年,William Parry带着英国海军的两艘船在近岸的冰层中过冬。1867年和1868年,美国探险家Charles Francis Hall在寻找Franklin远征队幸存者时路过此地。1913年,法裔加拿大探矿者Alfred Tremblay短暂访问,1921年Peter Freuchen作为Knud Rasmussen第五次图勒远征的一部分也曾到过这里。但这就是欧洲人接触的极限。
北极地区在1880年正式从英国统治转为加拿大统治,但Igloolik的首次持续接触直到1930年代天主教传教士到来才发生。他们的直接目标是摧毁萨满的权力和威望,萨满是文化支点,是因纽特人与宇宙关系的核心。为了促进同化,他们不鼓励使用传统姓名、歌曲和语言本身。像往常一样,贸易商品极具诱惑力,将人们吸引到传教站,远离土地,这一过程得到了政府当局的鼓励,到1950年代政府已经完全确立了存在。一场犬瘟热疫情让当局找到理由大规模屠杀因纽特人的狗。1960年代初雪地摩托的引入增加了对现金经济的依赖。家庭津贴的发放以儿童入学为条件,创造了定居的另一个激励。政府进行了人口普查,由于Inuktitut姓名很难转录,他们用数字标识每个因纽特人,发放身份标签,最终进行了”姓氏行动”,一个为从未有过姓氏的个人分配姓氏的奇异努力。不少因纽特人的狗被记录为加拿大公民。最后一击发生在1950年代,政府为对抗肺结核爆发,强制将每个因纽特人疏散到医院船上进行筛查。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大约五分之一,立即被送往南方治疗,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对被疏散者和留下者的心理影响都很深刻,与儿童被强制从家中带走接受教育时家庭承受的痛苦并无不同。在六岁和八岁时,Theo和John被送到南方800公里外的Chesterfield Inlet寄宿学校,在那里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Theo还遭到了牧师的性侵,他们在那里待了七年。
当他们终于被允许回家时,他们的家人立即带他们到土地上,Theo今天描述这是一次拯救任务。他回忆说,经过数年时间,“他们把我们重新变回了因纽特人。”
他重生的高潮是一次史诗般的狗拉雪橇之旅,从Igloolik出发,穿越巴芬岛,沿着埃尔斯米尔岛海岸向北,穿过史密斯海峡到达格陵兰岛,全程1800公里。Theo认为他可能有亲戚住在Qaanaaq这个小因纽特社区,这是世界上最北的定居点。事实证明他确实有,都是传奇萨满Qitdlarssuaq的后代,以及一个由六个家庭组成的小群体,他们在1850年代向北迁移,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到达格陵兰岛。Theo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这趟旅程。Andy和我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返回,乘坐仅需六小时的包机。飞机几乎立即飞越巴芬岛,我们从Theo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有什么不对。那是四月,我们的飞行路径在北极以南12度。海冰不在那里。Theo曾用雪橇狗穿越的史密斯海峡现在是开放水域。他难以置信地凝视着机窗外。眼中涌出泪水,他对没有特定对象说:“冰应该在十月份就结冰了。今年直到二月才结冰。Igloolik有知更鸟。我们甚至没有描述这些鸟的词汇。”
因纽特人是冰的民族。作为猎人,他们依靠冰生存,冰也激发了他们性格和文化的本质。在格陵兰岛极地爱斯基摩人中生活了八年的Gretel Ehrlich认为,正是冰的本质,它随季节移动、退缩、融化和重新形成的方式,赋予了因纽特人内心和精神如此的灵活性。她解释说:“他们对永恒没有幻想。没有时间后悔。绝望是对想象力的罪过。他们的杂货店就在外面的土地上,这创造了比城市居民大得多的情感生活。他们每天都在面对死亡。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杀死他们最爱的东西。冰上的血不是死亡的标志,而是生命的肯定。吃肉成为一种神圣的体验。”
格雷特尔在我们降落时就在卡纳克等着我们。和她在一起的是延斯·丹尼尔森,她在北方的导师,一个身材魁梧、心胸宽广、狩猎技能高超的男人。像西奥一样,延斯也曾带着狗进行过史诗般的旅程,他的情况是重走了拉斯穆森第五次图勒探险队的路线,从格陵兰岛穿越加拿大北部一直到遥远的阿拉斯加。在这两位杰出人物延斯和西奥的陪伴下,我们计划在冰上度过两周时间,在克克塔苏阿克岛西岸外建立一个狩猎营地,距离卡纳克大约两天路程。我们将乘坐狗拉雪橇前往那里。在北极所有因纽特社区中,只有卡纳克很久以前就禁止使用雪地摩托。人们明智地认识到,饲养雪橇犬是他们文化的支点。狗解开了束缚家庭与现金经济的枷锁。它们让任何旅程的长度变得无限。它们磨练了猎人的技能,猎人必须提供持续的肉类供应。它们为夜晚带来安全感。正如延斯所说,如果你是狗的主人,你就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在乘坐kamatiks以高速行驶数百公里,伴随着发动机持续的高音尖啸声之后,以狗队缓慢而稳定的步伐在春季冰面上前行是纯粹的快乐。这是如梦般的移动,是钢制滑板在柔软雪面上滑行时的寂静诗意。大地似乎从地平线上升起,奇怪的是,这让我想起了Hokule’a和航海者们,以及奈诺亚总是如何描述独木舟作为神圣的中心,它本身从不移动,因为船只等待着岛屿从海中浮现。西奥和延斯本身就是导航员,不仅导航他们土地的地理,也导航他们自己和他们人民的文化生存。西奥在一周前一场猛烈的暴风雪中告诉我,在北极是不可能迷路的,那场暴风雪遮蔽了天空,迫使我们八个人在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胶合板避难所里蜷缩了三天。当西奥烹饪北极嘉鱼时,延斯回忆起他杀死的21头北极熊,以及另外十几头差点杀死他的熊。你所要做的就是读懂雪。盛行风使所有的雪堆,无论大小,都指向西北方。在黑暗中,即使高速奔跑,西奥只需在地面上拖一只脚就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结果证明,一旦我们到达克克塔苏阿克岛,狗的价值就有限了。冰层中有巨大的开放水道,我们不得不乘船狩猎。延斯感到震惊。他从未在四月见过开放水域。在他的语言中,sila这个词既意味着天气,也意味着意识。天气带来动物或把它们赶走,让人们生存或导致他们死亡。延斯解释说,冰层过去在九月形成,一直保持坚固到七月。现在它在十一月到来,三月就消失了。狩猎季节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削减了一半。格雷特尔告诉我她和延斯去年夏天的一次旅行。他们在狩猎独角鲸,每天都下雨。一个下午他们独自站在岬角上,眺望大海。“这不是我们的天气,”延斯说道。“它从哪里来?我不明白。”
这就是北极的悲剧,也许也是北极的希望所在。一个承受了如此多苦难的民族——流行病、寄宿学校的羞辱和暴力、福利制度固有的贫困文化、酒精和药物暴露导致的自杀率是加拿大南部的六倍——现在正值他们在政治、社会和心理上重生的前夜,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股超出他们抵抗能力的力量。冰层正在融化,很可能一种生活方式也随之消失。
希望在于危机的严重性。今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城市物种。在1820年,只有伦敦的人口超过一百万。今天有414个这样规模或更大的城市,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在35年内将有超过1000个这样的城市,许多都遵循像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这样地方的模式,该城市1955年人口为47万,预计到2015年将有超过1600万居民。在城市空间中隔离和孤立,在许多情况下已经生活在有毒条件下,城市居民不会是第一个注意到全球气候变化后果的人。近十五年前,我和一位因纽特长者伊皮利·库努坐在巴芬岛的岸边,看着他用象牙海鸥的羽毛仔细清洁他的雪地摩托发动机化油器。他不会说英语,我也不懂因纽特语。但在奥拉尤克的翻译下,伊皮利当时告诉我,整个北极的天气变得更加狂野,太阳每年都更热,因纽特人第一次遭受皮肤疾病的困扰,正如他所说,是由天空引起的。
气候变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65万年来的最高水平。海洋变得更加温暖和酸性,作为海洋食物链基础的浮游动物,其数量自1960年以来已下降了73%。世界各地的自然栖息地都面临威胁,包括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亚洲草原的草地、亚马逊的低地雨林,以及从非洲之角到毛里塔尼亚大西洋海岸的整个撒哈拉以南干旱带。世界上一半的珊瑚礁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濒临崩溃。北美历史上已知最大规模的昆虫侵袭摧毁了美国西部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过13万平方公里的黑松林被毁,现在已蔓延到阿尔伯塔省,威胁着亚北极地区的北方森林。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岛国面临海平面大幅上升的可能性,已为其全体人口的撤离制定了应急计划。
但可以说,最大的直接威胁来自作为世界所有大河发源地的山地冰原。在青藏高原,作为黄河、湄公河和长江、雅鲁藏布江、萨尔温江、萨特累季河、印度河和恒河源头的地方,至少自1950年以来就没有净积雪。这些冰川不仅在边缘退缩,而且从表面向下融化。保守估计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60%的冰川将消失。一半的人类依赖这些河流。仅在印度次大陆就有5亿人依靠恒河取水;对于8亿印度教徒来说,它是神圣的恒河母亲,最神圣的河流。在旱季,河流70%的水量来自以每年近40米的速度退缩的恒河源冰川。如果像目前预期的那样,冰川完全消失,恒河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变成季节性河流。人们不敢想象这对印度造成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后果。2007年,当数百名朝圣者来到位于海拔3800米、印度教最神圣圣地之一的克什米尔阿马尔纳特洞穴时,发现几代人来一直被视为湿婆神神圣形象的阴茎形冰笋已经融化,引发了骚乱。
在世界各地,那些在这场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的山区民众,不仅看到了气候变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还对这个问题承担起个人责任,其认真程度常常让我们感到羞愧。南美洲西海岸80%的淡水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冰川。这些冰川的退缩如此明显,以至于前往Qoyllur Rit’i朝圣的信徒们,相信山神愤怒了,不再将来自Sinakara的冰块带回他们的社区,放弃了完成朝圣神圣循环、让每个人都能从神的恩典中受益的互惠行为。在哥伦比亚的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mamos每个季节都观察着对他们来说是世界真正心脏的雪地和冰原的退缩。他们还注意到鸟类、两栖动物和蝴蝶的消失,以及正在干涸的páramos生态特征的变化。他们增加了仪式和政治活动,并正式呼吁年轻兄弟停止摧毁世界。在坦桑尼亚,Chagga人仰望着一座在一代人时间里失去了80%以上雪冠的山峰,询问当乞力马扎罗不再照耀这片古老大陆时,他们的田野和非洲的理念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表述有些缺陷,暗示我们遇到的这些非凡民族是某种残余、古老的声音,被困在时间中,在当代生活中最多只能发挥模糊的顾问作用。事实上,我在这些讲座中提到的所有文化——藏族和桑人、Arhuacos、Wiwas和Kogi、基奥瓦人、Barasana、Makuna、本南人、Rendille、Tahltan、Gitxsan、Wet’suwet’en、海达人、因纽特人,以及波利尼西亚的所有民族——都非常活跃,不仅为了他们的文化生存而奋斗,还要参与一场将定义地球生命未来的全球对话。目前有1500种语言聚集在互联网的篝火旁,而且这个数字每周都在增加。为什么要听取他们的声音?有很多理由,其中许多我在这些讲座中至少隐含地提到过。但总结起来,两个词就够了。气候变化。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家质疑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和影响,或质疑导致其发生的因素、决定和优先考虑。它的出现是因为某种特定世界观的后果。正如汤姆·哈特曼所写,我们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消耗世界的远古阳光。我们的经济模式是投射和箭头,而它们应该是循环。将有限星球上的永续增长定义为经济福祉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在进行一种缓慢的集体自杀。在治理和经济的计算中否认或排除违反生命生物支撑系统的成本,这是妄想的逻辑。
这些声音很重要,因为它们仍能被听到,提醒我们确实存在着其他选择,其他方式来引导人类在社会、精神和生态空间中定位。这并不是幼稚地建议我们抛弃一切并试图模仿非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要求任何文化放弃从科技天赋中获益的权利。而是从以下事实中汲取灵感和安慰:我们所走的道路并非唯一可行的路径,因此我们的命运并没有不可磨灭地写在一系列选择中——这些选择已被证明在科学上并不明智。世界各种文化的存在本身就见证了那些声称我们无法改变的人的愚蠢,而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栖息这个星球的方式。我的一个登山朋友曾告诉我,登顶珠峰最令人惊奇的事情是意识到地球上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早上起床,系好靴子,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一天内走进一个空气稀薄到人类无法生存的区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启示,对允许地球上生命存在的这层脆弱大气薄纱的全新视角。
几年前,我从廷巴克图向北行进1000公里深入撒哈拉沙漠,到达古老的陶德尼盐矿。我和一些朋友同事,包括多次踏上这个旅程的加拿大摄影师克里斯·雷尼尔,沿着曾经定义西非商业的骆驼商队路线前进。在葡萄牙人找到横渡贝宁湾的航路,西班牙人发现并掠夺美洲财富之前,欧洲三分之二的黄金从加纳和非洲海岸陆路运输,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摩洛哥需要52天。位于马里的廷巴克图,距离尼日尔河大弯曲处一天的路程,成为了西部沙漠这片沙海上最重要的港口。在巴黎和伦敦还是中世纪小镇的时候,廷巴克图是一个拥有10万人口的繁荣中心,有150所学校和大学,约25000名学生学习天文学和数学、医学、植物学、哲学和宗教。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并驾齐驱,它是伊斯兰文化和学术的伟大中心之一。古希腊的知识得以保存并启发文艺复兴,只是因为它被伟大的伊斯兰学者如阿维森纳记录和保存下来,阿维森纳的著作让圣托马斯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和哲学。在廷巴克图,我手中拿着一份用金子装饰的文件,这是13世纪从阿维森纳1037年写成的手稿复制而来的。
今天的廷巴克图是一个大多令人遗忘的地方,干燥多尘,热得令人难以忍受。1914年,当法国人控制这座城市时,他们没收了古代手稿,威胁学者入狱,教导孩子们他们的祖先不是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不是塔马舍克人或图阿雷格人,而是高卢人。他们还打击盐贸易,用来自马赛的廉价海盐充斥市场,这不是出于经济竞争,而是因为传统贸易的象征意义。陶德尼的盐是撒哈拉的黄金,在整个西非因其治疗特性而受到重视,围绕其交换而发展起来的流动文化定义了这个民族。直到一个阿拉伯男孩忍受干渴和贫困,穿越沙漠——骑骆驼往返各需二十天——他才能结婚或被认为是男人。廷巴克图的一位老教授萨勒姆·乌尔德将这个旅程描述为力量的考验,一种让孩子成为感官大师的身体和精神转变。他说:“在无边的沙海中,年轻人意识到有比他自己更伟大的东西,他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粒子,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在调节这个世界。因此唤醒了寻求的渴望。当他们前往盐矿时,他们呼唤真主的神圣名字。沙漠磨砺他们的虔诚。”
我们旅程的向导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巴巴·乌马尔,他因为仅凭无线电中对一队迷路的外籍兵团士兵所在位置沙土气味和颜色的描述就找到了他们而闻名。这个故事并没有让乌尔德教授感到惊讶。“他们了解沙漠就像水手了解大海一样。当风吹起时,他们知道是什么样的风。当云聚集时,他们能闻到雨的味道。如果渴了,他们能感觉到水的气味。与骆驼之间建立的信任基于两千年的传统。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闭上眼睛,骆驼会带领他们回家。撒哈拉有一门科学,为那些穿越它几个世纪的人所知。”
我们乘吉普车向北行驶,巴巴有时相当急切地指着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而我们的司机在坚硬的白色平地上疾驰。当我们减速穿过松软的沙地,或在井边取水时,他注意沙丘的方向、沙土的颜色和质地、风在沙漠植物背风面形成的图案。他带着一个旧的法式军用指南针,不时趴下来测方位。然而,他真正的指南针显然在内心。当被问及是否曾经迷路时,他回答说在沙漠中定位是给少数人的天赋,如果他曾经不确定,他就简单地静坐等待真主的指引。
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两个非凡的事件。矿场本身就是一幅圣经般的景象,挖掘出的土堆绵延数公里,横跨在古老湖床的平坦地平线上。男人们脱去上衣,皮肤被盐分侵蚀开裂,在地下坑洞的洞穴般裂缝中用镐头凿开一块块盐板。我们的图阿雷格同伴伊萨·穆罕默德看了一眼说:“我不会带我妻子来这个地方。”当我询问一群男人的国籍时,他们回答:“这里没有国界。”
在矿场的最后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困于羞耻、背负债务的男人,他的身体虽然比我年轻,却被二十五年的矿坑生活摧残。他独自住在一间用粗盐块搭建的小房间里。他仅有的财产是一个生锈的油桶和他破烂的伯努斯——一件带兜帽的粗羊毛斗篷,为他的脸庞提供遮蔽和阴影。他有着羚羊般的眼睛。在这个季节性矿场800年的历史中,他是唯一一个已知在此度过夏天的人。他靠夜间工作生存,黎明前悄悄离开,走到远处的井边,独自坐在那里度过整天,在可以融化沙子的高温中。他的债务——让他受苦如此之久,让他与家人分离二十年的义务——还不到多伦多一家高档餐厅晚餐的费用。克里斯和我非常谨慎地给了他钱。他只是说:“愿上帝保佑。”当我们离开他的陋室时,一场沙暴席卷了矿场,像面纱一样包围了他。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或者他是否被殴打和抢劫,或者也许真的买到了自由。
在返回廷巴克图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在北行路上超过的一支商队。袭击我们到达陶德尼当晚营地的反常雷暴显然席卷了整个国家。如果盐受潮,就会碎裂并失去所有价值,所以年轻人被迫在沙漠中停下来,在阳光下晾干盐板。他们损失了关键的三天,当我们遇到他们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两夸脱的水。六个人距离最近的井还有150公里,带着珍贵的货物和二十多头骆驼,这代表了他们家庭的全部财富。没有恐慌的迹象。当我们停下时,我看到他们的一个伙伴带着一头骆驼在东方地平线上如海市蜃楼般闪烁。显然他们知道地面上有一个凹陷处,距离约25公里,如果挖到足够的深度可能会出水。
没有食物,身体可以存活数周;没有水,只能存活几天。在沙漠中缺水的情况下,谵妄在傍晚到来,到了早晨,嘴巴张开迎接风沙,即使眼睛沉入另一个现实,肺部发出奇异的吟唱声。撒哈拉的卡车走私者说,刹车油的好处是它能让你远离电池酸液。
在等待他们的朋友归来时,队伍的领袖穆罕默德生起一堆小火,用他们最后的水储备为我们沏茶。撒哈拉有句话说,如果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帐篷前,你会宰杀最后一只为你的孩子提供唯一牛奶来源的山羊来款待客人。人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成为那个在夜里出现的陌生人,寒冷饥饿,干渴需要庇护。当我看着穆罕默德为我倒茶时,我心想,正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怀抱希望。
当最初被邀请做马西讲座时,我既感到深深的荣幸,也有些犹豫,因为我已经出版了一本短书《世界边缘的光》(温哥华:道格拉斯与麦金太尔出版社,2007年;最初于2001年作为摄影集出版),它既是马西讲座的理想长度,也是关于吸引CBC关注我工作的议题和主题的宣言。我担心这口众所周知的井可能已经干涸。事实证明,这个挑战是理想的,因为它迫使我重新思考旧观念,同时为探索我经历中的许多新内容提供了平台。
我首次写到语言消失是在一本散文集《云豹》中,道格拉斯与麦金太尔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导致了一篇文章”消失的文化”,发表在1999年8月的《国家地理》上。2000年,我被邀请加入国家地理学会担任驻会探险家,任务是帮助学会改变世界看待和重视文化的方式。我创造了”民族圈”这个术语,以激发人们对这个包围地球的非凡文化矩阵的新思考方式。但我们如何才能真正产生影响呢?当生物学家确定一个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关键重要性的区域时,他们会创建一个保护区。人们无法指定一个心灵的雨林公园。作为一名完全了解文化动态、不断变化本质的人类学家,我对保存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我只是相信——正如我在哈佛的导师大卫·梅伯里-刘易斯曾经说过的——所有民族都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认识到论战很少能说服人,但怀着讲故事的人能改变世界的希望,我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带领《国家地理》的全球观众——165个国家的数亿人——前往ethnosphere中那些信仰、实践和直觉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让人们不得不以全新的眼光来欣赏人类想象力在文化中体现的奇迹。我的目标不是记录异域的他者,而是识别那些具有深刻隐喻共鸣的故事,那些关于生存本质的普遍真理。我们不仅仅是以电影制作者和民族志学者的身份进入这些社区;我们被当作合作者受到欢迎,建立在往往可以追溯到三十年或更久的关系和友谊网络基础上。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为土著声音提供一个平台,同时我们的镜头揭示思想、精神和适应的内在视野,这些视野可能会激发,用托马斯·贝里神父的话说,对地球的全新梦想。
这些讲座中涉及的许多主题,以及所描述的经历,都源自这些电影项目——总共十五部纪录片,在过去七年中与各位同事一起拍摄。在《世界边缘之光》系列中,我前往夏威夷、马克萨斯群岛、拉帕努伊和塔希提拍摄《寻路者》;前往格陵兰和努纳武特,在《北方冰原的猎人》中记录气候变化对因纽特世界的影响;前往喜马拉雅山反思西藏佛教和《心灵科学》;前往秘鲁探讨《神圣地理学》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组四部电影为阿鲁瓦科人和《魔法山》中的长老兄弟们发声,在《风马》中赞美蒙古的游牧民族,在《梦想守护者》中探索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哲学,在《亚马逊之心》中访问了巴拉萨纳人的家园。其他电影项目还带我们前往撒哈拉沙漠、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瓦哈卡的山区、大峡谷的深处以及哈瓦苏派和华拉派、祖尼、霍皮、派尤特和纳瓦霍人的家园。《世界边缘之光》的前四部电影可从史密森尼网络购买DVD。后四部电影将适时通过国家地理频道提供。
关于语言消失和复兴有大量且不断增长的文献。尽管物种灭绝的估计总是引发争议和生物学家之间的不同观点,语言学家们似乎普遍认为世界上一半的语言面临危险,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失。这种学术共识本身就令人不安。最近的著作包括:Andrew Dalby的《濒危语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3);David Crystal的《语言死亡》(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K. David Harrison的《当语言死亡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Leanne Hinton和Ken Hale编辑的《语言复兴实践绿皮书》(圣地亚哥:学术出版社,2001);Joshua Fishman编辑的《濒危语言能否被拯救?逆转语言转移,重新审视:21世纪视角》(英国克利夫登:多语言事务出版社,2001);Daniel Nettle和Suzanne Romaine的《消失的声音》(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以及Nicholas Ostler的《词语帝国:世界语言史》(纽约:哈珀柯林斯,2005)。
关于已知语言的目录,参见:Raymond G. Gordon, Jr.编辑的《民族语言学:世界语言》第15版(达拉斯:国际夏季语言学研究所,2005),以及David Crystal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第2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关于语言、景观、知识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参见:Luisa Maffi编辑的《论生物文化多样性》(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出版社,2001)。
我对人口遗传学启示的理解深深受惠于Spencer Wells,他是《深度血统:基因地理项目内部》(华盛顿特区:国家地理图书,2006)和《人类之旅》(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的作者,后者是一本精彩的书,源于同名PBS电影。我在1970年代初作为哈佛大学Irven DeVore的年轻学生时首次接触卡拉哈里布什曼人。当时没有人能想象有一天科学会揭示San人是我们家族树的根干,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这看起来就像声称已经确定了伊甸园的实际地点一样荒谬。但即使是这个原始的起源点也已被有效找到,我们物种离开非洲的出发门户也已被精确发现。最早预见这一非凡研究途径的是Spencer的导师Luigi Luca Cavalli-Sforza,《基因、民族和语言》一书的作者(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
对于研究桑族的经典民族志著作,参见:Richard B. Lee 和 Irven DeVore 主编,《卡拉哈里狩猎采集者》(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和 Richard B. Lee 的《!Kung 桑族》(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两本引人入胜的旅行记录参见:Laurens van der Post 的《卡拉哈里的失落世界》(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7),和 Rupert Isaacson 的《治愈之地》(New York: Grove Press, 2001)。有许多精美的图文并茂的书籍,但其中最好的之一是 Alf Wannenburgh 的《丛林人》(Cape Town: Struik Publishers, 1979),由 Peter Johnson 和 Anthony Bannister 摄影。
Thomas Whiffen 的书《西北亚马逊:在食人族部落中度过数月的记录》于 1915 年在伦敦由 Constable 出版。另见 Eugenio Robuchon 的《在普图马约及其支流》(Lima: Imprenta la Indústria, 1907),和 Michael Taussig 的《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关于 Steven Pinker 的引用,参见”我的基因组,我的自我”,《纽约时报杂志》(2009年1月11日)。Spencer Wells 在《人类的旅程》中引用的 Carleton Coon 的两本书是《种族的起源》(New York: Knopf, 1962) 和《人类的现生种族》(New York: Knopf, 1965)。柯松勋爵在 James Morris 的《告别号角》(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中被引用,塞西尔·罗德斯在 Brian Moynahan 的《英国世纪》(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中被引用。
Clayton Eshleman 和他的妻子 Caryl 向我介绍了上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并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笔记,这些笔记反过来来源于 Clayton 的杰出著作《杜松融合:上旧石器时代的想象力与地下世界的构建》(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3)。关于上旧石器时代的其他资料,参见:Paul Bahn 和 Jean Vertut 的《穿越冰河时代》(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Paul Bahn 的《剑桥史前艺术图解史》(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Dale Guthrie 的《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本质》(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André Leroi-Gourhan 的《史前艺术珍宝》(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67);和 Sigfried Giedion 的《永恒的现在:艺术的起源》,Bollingen Series 35, 6.1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2)。关于 Northrop Frye 参见:《可怖的对称》(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重印,1969) 和《英国浪漫主义研究》(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关于马克萨斯群岛的文化冲突,参见:Edwin Ferdon 的《马克萨斯文化的早期观察,1595-1813》(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3);David Porter 的《太平洋航海日记》,2卷本 (1822; 重印,Upper Saddle River, N.J.: The Gregg Press, 1970);Greg Dening 的《岛屿与海滩:沉默之地的话语,马克萨斯 1774-1880》(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0);Greg Dening 主编的《爱德华·罗伯茨的马克萨斯日记,1797-1824》,太平洋历史系列,第6号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4);E. S. Craighill Handy 的《马克萨斯的本土文化》,伯尼斯·P·毕晓普博物馆公报第9号 (Honolulu: Bernice P. Bishop Museum, 1923);Nicholas Thomas 的《马克萨斯社会:东波利尼西亚的不平等与政治变革》(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和 Willowdean Handy 的《永远的男人之地:马克萨斯群岛访问记》(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65)。
关于甘薯的经典记述,参见:D. E. Yen 的《甘薯与大洋洲:民族植物学论文》,伯尼斯·P·毕晓普博物馆公报第236号 (Honolulu: Bishop Museum Press, 1974)。关于在智利南海岸前哥伦布时期的 El Arenal 遗址发现鸡骨的报道,参见:《自然》杂志 447, 620-621 (2007年6月)。
关于太平洋的考古学,最好的书是:Patrick Vinton Kirch 的《风之路上:欧洲接触前太平洋岛屿的考古史》(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我认为 Kirch 的所有作品都非常出色。参见他写的另外两本书——《波利尼西亚酋长制的演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和《拉皮塔人:大洋世界的祖先》(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以及以下合著作品:Patrick Vinton Kirch 和 Jean-Louis Rallu 主编的《太平洋岛屿社会的增长与衰落:考古学与人口学视角》(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和 Patrick Vinton Kirch 与 Roger Green 的《夏威基,祖先波利尼西亚:历史人类学论文》(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波利尼西亚航海的专著和记录,参见:大卫·刘易斯,《我们,航海者:太平洋寻陆的古老艺术》(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2年);大卫·刘易斯,《航海之星:太平洋岛屿航海者的秘密》(纽约:W. W. Norton出版社,1978年);托马斯·格拉德温,《东方是一只大鸟:普卢瓦特环礁的航海与逻辑》(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斯蒂芬·托马斯,《最后的航海者》(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87年);理查德·费因伯格,《波利尼西亚航海与导航:阿努坦文化和社会中的海洋旅行》(俄亥俄州肯特: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88年);以及理查德·费因伯格编,《当代太平洋岛屿的航海:连续性与变化研究》(德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5年)。
彼得·巴克的经典著作是《日出的维京人》(1938年;重印版,新西兰基督城:惠特库姆与汤姆斯出版社,1954年)。安德鲁·夏普在《波利尼西亚的古代航海者》(伦敦:企鹅图书出版社,1957年)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关于意外漂流的争议性观念促成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聚会,产生了一部论文集:杰克·戈尔森编,《波利尼西亚航海:关于安德鲁·夏普意外航行理论的研讨会》(新西兰惠灵顿:A. H. 和 A. W. 里德为波利尼西亚学会出版,1963年)。
夏威夷大学的开创性人类学家本·芬尼写了一篇关于神圣独木舟首次实验航行的记录:《霍库莱阿:通往塔希提之路》(纽约:多德·米德公司,1979年)。关于这段复杂而鼓舞人心的历史,更多内容可以在波利尼西亚航海学会的优秀网站上找到:http://pvs.kcc.hawaii.edu/aboutpvs.html。
托尔·海尔达尔在《阿库-阿库: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表达了他对拉帕努伊和波利尼西亚历史的错误解释,该书恰如其分地由兰德·麦克纳利出版社(芝加哥,1958年)出版。他的《康提基号:乘筏横渡太平洋》(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64年),最初发表于1950年,作为大众市场平装本仍有售,并已有65种语言版本。海尔达尔关于复活节岛的观点被托马斯·巴塞尔在《第八块土地:波利尼西亚人发现和定居复活节岛》(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8年)中彻底驳斥。基于一个杰出的智利学者团队30多年研究的最佳单一考古资料,不幸尚未翻译成英文:帕特里西亚·巴尔加斯、克劳迪奥·克里斯蒂诺和罗伯托·伊扎乌列塔,《拉帕努伊的1000年:定居考古学》(圣地亚哥:智利大学大学出版社,2006年)。埃德蒙多·爱德华兹与帕特里西亚和克劳迪奥一起在岛上发掘了约25,000个遗址,即将出版他的毕生之作。虽然埃德蒙多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花粉研究,揭示了波利尼西亚人到达时特有植物群的特征,但他们否认岛屿文明突然崩溃的观念,这种观念已被广泛发表,几乎成了环保运动的寓言。他们的工作表明这是一个处于转型中的文化,鸟人崇拜不是衰落和衰败的标志,而是重塑和变革的象征,这一进程被欧洲人接触带来的疾病和其他可怕后果粗暴地中断了。
弗朗西斯·威多森和阿尔伯特·霍华德写了《剥下原住民产业的外衣:原住民文化保护背后的欺骗》(蒙特利尔: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是一本既苦涩又无知的书。关于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和弗兰茨·博厄斯的优秀传记,参见:道格拉斯·科尔,《弗兰茨·博厄斯:早年岁月,1858-1906》(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迈克尔·杨,《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库拉的经典著作是:《西太平洋的远航者: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群岛土著企业和冒险记录》(伊利诺伊州长格罗夫:韦夫兰出版社,1984年)。该书首次出版于1922年,是人类学的伟大经典之一。他还写了其他几本书,包括《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英属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求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民族志记录》(伦敦:乔治·劳特利奇父子出版社,1932年)。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有争议的田野日志,参见:《严格意义上的日记》(1967年;重印版,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关于库拉象征表现的优秀著作,参见:雪莉·坎贝尔,《库拉的艺术》(牛津:伯格出版社,2002年)。
关于奥雷利亚纳与亚马逊女战士相遇的引人入胜描述,请参阅:Alex Shoumatoff,In Southern Light(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6年)。加斯帕尔·德·皮内尔(Gaspar de Pinell)驻扎在普图马约河源头的西班多伊嘉布遣会传教站。他的报告Excursión Apostólica por los Ríos Putumayo, San Miguel de Sucumbíos, Cuyabeno, Caquetá y Caguán于1928年由波哥大国家印刷厂出版。朱利安·达圭德(Julian Duguid)的《绿色地狱:玻利维亚东部森林旅行记》于1930年在伦敦出版,由乔治·纽尼斯有限公司出版。这类书籍很多。我本人关于热带生态学和亚马逊雨林脆弱性的评论发表在论文集The Clouded Leopard中(温哥华:Douglas & McIntyre出版社,1998年)。但我们都已经照本宣科地重复这些观点二十多年了。
关于欧洲接触前美洲特别是亚马逊地区的全面深刻调查,请参阅:查尔斯·曼(Charles Mann),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2006年)。关于查尔斯·玛丽·德·拉·孔达明(Char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请参阅:Viaje a la América Meridional por el Río de las Amazonas(1743年;重印版,巴塞罗那:Editorial Alta Fulla出版社,1986年)。关于接触的后果,请参阅:罗纳德·赖特(Ronald Wright),Stolen Continents: The Americas Through Indian Eyes Since 1492(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92年)。保罗·理查兹(Paul Richards)的经典著作是The Tropical Rain Forest: An Ecological Study(纽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52年)。关于我本人在安第斯山脉和亚马逊西北地区的旅行、与蒂姆·普洛曼(Tim Plowman)关于古柯的工作以及后续的植物学探索,请参阅:One River: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Amazon Rain Forest(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96年)。
关于贝蒂·梅格斯(Betty Meggers)和安娜·罗斯福(Anna Roosevelt)之间的争论,请参阅查尔斯·曼在1491(如上所引)中的精彩讨论,以及:贝蒂·梅格斯,Amazonia: Man and Culture in a Counterfeit Paradise(阿灵顿高地,伊利诺伊州:AHM出版公司,1971年);安娜·罗斯福,Moundbuilders of the Amazon: Geophysical Archaeology on Marajó Island, Brazil(圣地亚哥:Academic Press出版社,1991年);以及安娜·罗斯福编辑,Amazonian Indian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图森: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出版社,1994年)。关于亚马逊的新思维,请参阅比尔·德内万(Bill Denevan)的几篇出版物:W. M. Denevan,Cultivated Landscapes of Native Amazonia and the Andes(纽约: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2001年);W. M. Denevan编辑,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麦迪逊: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出版社,1976年);“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Amazonia in 1492 Reconsidered”,Revista de Indias 62,第227期(2003年):175-88;“The Pristine Myth: The Landscape of the Americas in 1492”,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1992年):369-85;以及”Stone vs. Metal Axes: The Ambiguity of Shifting Cultivation in Prehistoric Amazonia”,Journal of the Steward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20(1992年):153-65。关于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关于石制工具效率的研究,请参阅:“Tree Felling with the Stone Axe: An Experiment Carried Out Among the Yanomamö Indians of Southern Venezuela”,载于Carol Kramer编辑,Ethnoarchaeology: Implications of Ethnography for Archaeology(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79年),21-58。关于征服后技术和农产品交流的经典叙述是: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韦斯特波特,康涅狄格州:Greenwood Press出版社,1972年)。另请参阅克罗斯比的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86年)。
在过去四十年中,一小群杰出的人类学家在哥伦比亚亚马逊西北地区的民族中开展工作,其中一些是该专业最受尊敬的民族志学者。先驱者是赫拉尔多·赖歇尔-多尔马托夫(Gerardo Reichel-Dolmatoff),他是我的教授理查德·埃文斯·舒尔茨(Richard Evans Schultes)的密友和同代人,舒尔茨本人花了十二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该地区的民族植物学。舒尔茨著有10本书和496篇科学论文。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治疗森林:亚马逊西北地区的药用和有毒植物》,与罗伯特·拉福(Robert Raffauf)合著(俄勒冈州波特兰:Dioscorides Press出版社,1990年);The Botany and Chemistry of Hallucinogens,与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合著,第2版修订增补版(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Charles C. Thomas出版社,1980年);《众神的植物》,与阿尔伯特·霍夫曼合著(纽约:McGraw-Hill出版社,1979年)。关于死藤水(ayahuasca)有大量文献,其中很多由丹尼斯·麦肯纳(Dennis McKenna)撰写。最佳单一论文集,包括舒尔茨、麦肯纳、让·兰登(Jean Langdon)、布朗温·盖茨(Bronwen Gates)、路易斯·卢纳(Luis Luna)和安东尼·亨曼(Anthony Henman)的贡献,请参阅:América Indígena 46(1)(1986年):5-256。
Reichel-Dolmatoff的著作包括:《亚马逊宇宙观:图卡诺印第安人的性与宗教象征主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内在森林:亚马逊图卡诺印第安人的世界观》(英国福克斯霍尔:Themis Books,1996年);《雨林萨满:西北亚马逊图卡诺印第安人论文集》(英国福克斯霍尔:Themis Books,1997年);以及《萨满与美洲豹:哥伦比亚印第安人麻醉药物研究》(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75年)。另见:Jean Jackson,《鱼人:西北亚马逊地区的语言外婚制与图卡诺身份认同》(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Kaj Arhem,《马库纳社会组织》(斯德哥尔摩: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1981年);以及Irving Goldman,《库贝奥·赫赫内瓦宗教思想》,由Peter Wilson死后编辑出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Stephen和Christine Hugh-Jones于1968年首次在巴拉萨纳人中生活。两人都写了开创性的专著。见:Christine Hugh-Jones,《来自牛奶河:西北亚马逊的空间与时间过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以及Stephen Hugh-Jones,《棕榈与昴宿星团:西北亚马逊的成人礼与宇宙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Christine后来学习和从事医学,但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多次返回皮拉帕拉纳河,巴拉萨纳人及其邻居显然将他们视为受人尊敬的长辈。执导《魔山》的Graham Townsley和执导《风马》与《亚马逊之心》的Howard Reid都在剑桥大学Stephen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
关于皮拉帕拉纳河信仰与传统最优秀的当代著作之一是由该河流土著民族所写。见:Kaj Arhem、Luis Cayón、Gladys Angulo和Maximiliano García,《马库纳民族志:水之民的传统、故事与智慧》(波哥大:哥伦比亚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2004年)。Kaj Arhem与摄影师Diego Samper合作出版了一本精美的插图书《马库纳:亚马逊民族肖像》(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98年)。关于盖亚亚马逊基金会的工作,见:Martin von Hildebrand,“盖亚与文化:哥伦比亚亚马逊的互惠与交换”,载于Peter Bunyard编,《行动中的盖亚,生命地球科学》(爱丁堡:Floris Books,1996年)。网站为:www.gaiaamazonas.org。
关于神圣源头以及塔尔坦人保护其在斯蒂金河流域家园的努力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www.skeenawatershed.com和www.sacredheadwaters.com。我在海达瓜伊的伐木营地待了一年,并在《云豹》(温哥华:Douglas & McIntyre,1998年)中发表的文章”在红雪松的阴影中”记录了这一经历。
关于古柯文化重要性的两本优秀著作,见C. J. Allen,《生活的牵绊:安第斯社区中的古柯与文化认同》(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88年),以及Anthony Henman,《古柯妈妈》(伦敦:Hassle Free Press,1978年)。
关于印加和当代安第斯民族志有大量文献。印加历史方面,见Louis Baudin,《最后印加统治下的秘鲁日常生活》(纽约:Macmillan,1968年);Brian Bauer的《印加国家的发展》(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古代库斯科:印加的心脏地带》(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4年);B. C. Brundage的《库斯科领主》(1967年)和《印加帝国》(1963年),均再版(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5年);R. Burger、C. Morris和R. Matos Mendieta编,《印加权力表现的变化:1997年10月18-19日敦巴顿橡树园研讨会》(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与收藏,2007年);G. W. Conrad和A. Demarest,《宗教与帝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T. D’Altroy,《印加人》(牛津:Blackwell,2002年);J. Hemming,《印加的征服》(纽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0年);C. Morris和A. von Hagen,《印加帝国及其安第斯起源》(纽约:Abbeville Press,1993年);M. Moseley,《印加人及其祖先:秘鲁考古学》(伦敦:Thames & Hudson,1992年);K. MacQuarrie,《印加人的最后岁月》(纽约:Simon & Schuster,2007年);A. Métraux,《印加人的历史》(纽约:Schocken Books,1979年);J. H. Rowe,“西班牙征服时期的印加文化”,载于J. H. Steward编,《南美印第安人手册》,美国民族学局公报143,第2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183-330页;以及R. T. Zuidema,《库斯科的印加文明》(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有关编年史早期记述的重印版本,参见:J. de Acosta,《印第安人的自然与道德历史》,Jane Mangan编辑(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J. de Betanzos,《印加叙事》,Roland Hamilton和Dana Buchanan翻译编辑(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6年);B. Cobo,《印加宗教与习俗》(1653年),Roland Hamilton翻译编辑(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B. Cobo,《印加帝国史》(1653年),Roland Hamilton翻译编辑(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Garcilaso de la Vega,《印加王室评论与秘鲁通史,第1-2部分》(1609年),Harold Livermore翻译(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6年);Poma Huamán Poma de Ayaala,《致国王的信》,Christopher Dilke编辑(纽约:Dutton出版社,1978年);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印加史》(1572年),Brian Bauer和Vania Smith翻译编辑(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7年);Pedro de Cieza de León,《印加人》(1554年),Victor W. von Hagen编辑(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76年)。
有关安第斯山脉的土地观念、朝圣和神圣地理学,参见:M. J. Sallnow,《安第斯朝圣者》(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87年);B. Bauer和C. Stanish,《古代安第斯的仪式与朝圣:太阳岛和月亮岛》(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B. Bauer,《印加的神圣景观:库斯科塞克体系》(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以及R. T. Zuidema,《库斯科的塞克体系:印加首都的社会组织》(莱顿:E. J. Brill出版社,1964年)。Johan Reinhard撰写了几本重要著作,包括《冰雪少女:印加木乃伊、山神和安第斯神圣遗址》(华盛顿特区:国家地理学会,2005年)和《马丘比丘:探索古代神圣中心》第4修订版(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院,2007年)。有关Qoyllur Rit’I的优秀研究,参见:Robert Randall,“Qoyllur Rit’I,昴宿星团的印加节日”,《法国安第斯研究所公报》第11卷,(1-2):37-81(利马)。
有关天文学,参见:Brian Bauer和David Dearborn,《古代安第斯的天文学与帝国》(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G. Urton,《在大地与天空的十字路口:安第斯宇宙论》(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有关印加道路,参见:J. Hyslop,《印加道路系统》(纽约:学术出版社,1984年),以及Victor W. von Hagen,《太阳之路》(波士顿:Little, Brown出版社,1955年)。另见J. Hyslop,《印加定居点规划》(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有关安第斯Khipu会计系统的优秀著作,参见:G. Urton,《印加Khipu的符号:安第斯结绳记录中的二进制编码》(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J. Quilter和G. Urton编辑,《叙事之线:安第斯Khipu中的记录与叙述》(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
有关经典民族志,参见:T. A. Abercrombie,《记忆与权力之路:安第斯民族的民族志与历史》(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8年);J. W. Bastien,《秃鹫之山:安第斯ayllu中的隐喻与仪式》(Long Grove,伊利诺伊州:Waveland出版社,1985年);Inge Bolin的《在尊重文化中成长:秘鲁高地的儿童养育》(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尊重的仪式:秘鲁安第斯高地生存的秘密》(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S. Brush,《山地、田野与家庭:安第斯山谷的经济与人类生态学》(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J. Meyerson,《坦博:安第斯村庄的生活》(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B. J. Isbell,《保卫我们自己:安第斯村庄的生态与仪式》(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以及F. Salomon,《结绳记录者:秘鲁村庄中的Khipus与文化生活》(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关维尔卡班巴——印加最后据点的历史,参见:H. Thomson,《白石:印加腹地探索》(纽约州伍德斯托克:Overlook出版社,2003年),以及V. Lee,《被遗忘的维尔卡班巴:印加的最后要塞》(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Empire出版公司,2000年)。
有关安第斯纺织传统,参见:Nilda Callañaupa Alvarez,《秘鲁高地编织:编织图案,编织记忆》(科罗拉多州洛夫兰:Interweave出版社,2007年)。有关安第斯民族植物学,参见:J. Bastien,《安第斯治疗师:Kallawaya草药师及其药用植物》(盐湖城:犹他大学出版社,1987年);C. Franquemont、T. Plowman、E. Franquemont等,《钦切罗的民族植物学:秘鲁南部的安第斯社区》,植物学新系列第24号(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1990年)。
有关当代秘鲁的精彩描绘,参见Ron Wright,《切石与十字路口》(纽约:企鹅图书,1984年)。有关一本极好且非常有趣的旅行记录,涵盖毒品贸易兴起之前的圣玛尔塔雪山山脉,参见:Charles Nicholl,《果实宫殿》(伦敦:Heinemann出版社,1985年)。
要了解长兄世界的深入信息,已故的赫拉尔多·赖歇尔-多尔马托夫(Gerardo Reichel-Dolmatoff)再次是一个基础资源。他的专著于1950年和1951年分两卷出版,1985年重印;参见《Los Kogi: Una Tribu de la 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 Colombia》,2卷本(波哥大:Nueva Biblioteca Colombiana de Procultura出版社,Editorial Presencia出版社,1985年)。此外,还可参见赖歇尔-多尔马托夫的以下著作:《The Sacred Mountain of Colombia’s Kogi Indians》(莱顿:E. J. Brill出版社,1990年);“Training for the Priesthood Among the Kogi of Colombia”,载于J. Wilbert编辑的《Encultu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 Anthology》(洛杉矶:UCLA拉丁美洲中心出版社,1976年);“The Loom of Life: A Kogi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Lore》第4卷第1期(1978年):5-27页;“The Great Mother and the Kogi Universe: A Concise Overview”,《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Lore》第13卷第1期(1987年):73-113页;“Templos Kogi: Introducción al Simbolismo y a la Astronomía del Espacio Sacrado”,《Revista Colombiana de Antropología》第19期(1975年):199-246页;以及《Indians of Colombia: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波哥大:Villegas Editores出版社,1991年)。关于阿鲁阿科(Arhuaco)神话和仪式,参见:唐纳德·泰勒(Donald Tayler)的《The Coming of the Sun》,皮特河流博物馆专著第7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另见:艾伦·埃雷拉(Alan Ereira)的《The Elder Brothers’ Warning》(伦敦:泰罗纳遗产信托基金,2009年)。1991年,艾伦·埃雷拉和格雷厄姆·汤斯利(Graham Townsley)制作了《From the Heart of the World》,这是一部将科吉人和长兄的信息传达给世界的有力影片。埃雷拉后来建立了泰罗纳遗产信托基金(www.tairona.myzen.co.uk),这是一个与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土著人民官方组织戈纳温杜阿(Gonawindua)(www.tairona.org)密切合作的非营利组织。
要理解梦境时代(Dreaming)和歌线(Songlines),我发现布鲁斯·查特温(Bruce Chatwin)的畅销书《The Songlines》(纽约:企鹅出版社,1988年)并不是很有帮助。对原住民文明微妙哲学最具启发性和优雅的探索是W. E. H. 斯坦纳(W. E. H. Stanner)的”The Dreaming”,收录在他的文集《White Man Got No Dreaming: Essays, 1938-1973》中(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9年)。其他经典著作包括:罗纳德·伯恩特(Ronald Berndt)和凯瑟琳·伯恩特(Catherine Berndt)的《The Speaking Land》(悉尼:企鹅图书,1988年)和《The World of the First Australians》(堪培拉:原住民研究出版社,1988年);A. P. 埃尔金(A. P. Elkin)的《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第4版(悉尼:安格斯与罗伯逊出版社,1976年);以及T. G. H. 斯特雷洛(T. G. H. Strehlow)的《Aranda Traditions》(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4年)和《Songs of Central Australia》(悉尼:安格斯与罗伯逊出版社,1971年)。另见:约翰·马尔瓦尼(John Mulvaney)和约翰·卡明加(Johan Kamminga)的《Prehistory of Australia》(圣伦纳兹,澳大利亚: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99年);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的《Land Is Life: From Bush to Town: The Story of the Yanyuwa People》(圣伦纳兹,澳大利亚: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99年);弗雷德·迈尔斯(Fred Myers)的《Pintupi Country, Pintupi Self: Sentiment, Place, and Politics among Western Desert Aborigine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罗伯特·汤金森(Robert Tonkinson)和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编辑的《Going It Alone?: Prospects for Aboriginal Autonomy》(堪培拉:原住民研究出版社,1990年);以及罗伯特·汤金森的《The Mardu Aborigines: Living the Dream in Australia’s Desert》(沃思堡,德克萨斯州:霍尔特、莱因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91年)和《The Jigalong Mob: Aboriginal Victors of the Desert Crusade》(门洛帕克,加利福尼亚州:本杰明·卡明斯出版公司,1974年)。
关于文化冲突及其后果,参见:布鲁斯·埃尔德(Bruce Elder)的《Blood on the Wattle: Massacres and Maltreatment of Aboriginal Australians Since 1788》(悉尼:新荷兰出版社,2002年);阿利斯泰尔·帕特森(Alistair Paterson)的《The Lost Legions: Culture Contact in Colonial Australia》(普利茅斯,英格兰: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8年)。关于原住民艺术的奇迹,参见:弗雷德·迈尔斯的《Painting Culture: The Making of a High Aboriginal Art》(达勒姆,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关于流行的调查和介绍,参见:罗伯特·劳勒(Robert Lawlor)的《Voices of the First Day: Awakening in the Aboriginal Dreamtime》(罗彻斯特,佛蒙特州:内在传统出版社,1991年)。
这一章的标题来自于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令人惊叹的三部曲第三卷《火的记忆》(Memory of Fire)(纽约:Pantheon Books出版社,1985,1987,1988)。关于伊甸园,参见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的文章”伊甸园?也许吧。但苹果树在哪里?“《纽约时报》(2009年4月30日)。另见:莎拉·蒂什科夫(Sarah Tishkoff)等人的”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遗传结构和历史”,《科学》324期,第5930号(2009年5月):1035-44页。关于马萨特克口哨语言,参见:G. M. 科万(G. M. Cowan)的”马萨特科口哨语言”,《语言》24期,第3号(1948年):280-86页。要了解伏都教的神秘领域,请参阅我的两本关于海地的书:《蛇与彩虹》(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5年)和《黑暗之路》(Passage of Darkness)(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关于纳西族,参见:蔡华的《没有父亲或丈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The Na of China)(布鲁克林:Zone Books出版社,2008年)。关于瓦拉奥人,参见:约翰内斯·威尔伯特(Johannes Wilbert)的《饥荒的记忆:瓦拉奥印第安人的宗教气候学》(Mindful of Famine: Religious Climatology of the Warao Indian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神秘天赋:瓦拉奥印第安人的宗教人种志》(Mystic Endowment: Religious Ethnography of the Warao Indian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南美洲的烟草与萨满教》(Tobacco and Shamanism in South America)(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门塔维美学,参见:查尔斯·林赛(Charles Lindsay)的《门塔维萨满:雨林守护者》(Mentawai Shaman: Keeper of the Rain Forest)(纽约:Aperture出版社,1992年)。
关于天台马拉松僧侣和山伏(Yamabushi)的传统,参见:卡门·布拉克(Carmen Blacker)的《梓弓:日本萨满教实践研究》(The Catalpa Bow: A Study of Shamanistic Practices in Japan)(伦敦:Allen & Unwin出版社,1975年);宫家准(Miyake Hitoshi)的《修验道:日本民间宗教结构论文集》(Shugendō: Essays on the Structure of Japanese Folk Religion)(密歇根州安娜堡:密歇根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01年);宫家准的《山的曼荼罗:修验道与民间宗教》(The Mandala of the Mountain: Shugendō and Folk Religion),关口ゲイナー(Gaynor Sekimori)编辑(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5年);保罗·斯旺森(Paul Swanson)编辑的《日本的天台佛教》,《日本宗教研究杂志》14期,第2-3号(1987年);罗伊·泰勒(Royall Tyler)和保罗·斯旺森编辑的《日本的修验道与山岳宗教》,《日本宗教研究杂志》16期,第2-3号(1989年);珀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的《神秘的日本》(Occult Japan)(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895年);以及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的《比叡山的马拉松僧侣》(The Marathon Monks of Mount Hiei)(波士顿:Shambhala出版社,1988年)。
要理解所有这些复杂的文化概念,最好的资料来源和最权威的声音是已故的戴维·梅伯里-刘易斯(David Maybury-Lewis),他教会了我几乎所有关于人类学的知识。请参阅他的经典著作:《阿克韦-沙万特社会》(Akwe-Shavante Society)(牛津:Clarendon Press出版社,1967年);《辩证社会》(Dialectical Societi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土著民族、族群与国家》(Indigenous Peoples, Ethnic Groups, and the State)(1965年;重印版,波士顿:Allyn and Bacon出版社,1997年);《野蛮人与无辜者》(The Savage and the Innocent)(波士顿:Beacon Press出版社,2000年);他编辑的作品《族群政治:拉丁美洲国家中的土著民族》(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tin American Stat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千禧年:部落智慧与现代世界》(Millennium: Tribal Wisdom and the Modern World)(纽约:Viking出版社,1992年)。
关于基奥瓦人,参见:J. 穆尼(J. Mooney)的”基奥瓦印第安人历法史”,《美国人种学局第十七次年度报告》(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898年),129-445页;《一条河》(One River)(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96年);韦斯顿·拉巴雷(Weston LaBarre)的《仙人掌崇拜》(The Peyote Cult)(1938年),第5版,扩充版(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9年)。关于系统性消灭野牛,参见:安德鲁·伊森伯格(Andrew Isenberg)的《野牛的毁灭:环境史,1750-1920》(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50-192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普图马约橡胶时代的恐怖,参见:诺曼·汤姆森(Norman Thomson)的《普图马约红皮书》(The Putumayo Red Book)(伦敦:N. Thomson & Co.出版社,1913年);R. 科利尔(R. Collier)的《上帝遗忘的河流》(The River that God Forgot)(伦敦:Collins出版社,1968年);W. E. 哈登伯格(W. E. Hardenburg)的《普图马约:魔鬼的天堂》(The Putumayo: The Devil’s Paradise)(伦敦:T. Fisher Unwin出版社,1912年);B. 温斯坦(B. Weinstein)的《亚马逊橡胶热潮,1850-1920》(The Amazon Rubber Boom, 1850-1920)(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
关于本南人的声音和马来西亚各官员的引述,参见: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伊恩·麦肯齐(Ian MacKenzie)和沙恩·肯尼迪(Shane Kennedy)的《黎明游牧者:婆罗洲雨林中的本南人》(Nomads of the Dawn: The Penan of the Borneo Rain Forest)(旧金山:Pomegranate Press出版社,1995年)。要支持布鲁诺·曼瑟(Bruno Manser)的遗产,请联系布鲁诺·曼瑟基金会,网址:www.bmf.ch/en/。另见:“翡翠森林之梦”,这是我为布鲁诺写的人物简介,后来发表在《云豹》(The Clouded Leopard)(温哥华:Douglas & McIntyre出版社,1998年),57-72页。
关于波尔布特(Pol Pot)和杀戮场,参见: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的《一号兄弟:波尔布特政治传记》(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科罗拉多州博尔德:Westview Press出版社,1999年);狄·普兰(Dith Pran)的《柬埔寨杀戮场的孩子们:幸存者回忆录》(Children of Cambodia’s Killing Fields: Memoirs by Survivors)(泰国清迈:Silkworm Books出版社,1997年);本·基尔南(Ben Kiernan)的《波尔布特如何上台:柬埔寨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1930-1975》(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ambodia, 1930-1975)(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波尔布特政权: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种族、权力与种族灭绝,1975-79》(The Pol Pot Regime: 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under the Khmer Rouge, 1975-79)(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龙·翁(Loung Ung)的《他们先杀了我父亲:一个柬埔寨女儿的回忆》(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 A Daughter of Cambodia Remembers)(纽约:Perennial出版社,2000年)。
关于中国革命以来西藏历史的最佳单一史料是:Tsering Shakya,《雪域之龙:1947年以来的现代西藏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见:M. C. Goldstein,《现代西藏史,1913-1951》(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及Tubten Khetsun,《中国统治下拉萨生活回忆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两本优秀的通俗历史著作是:Charles Allen,《寻找香格里拉:西藏历史之旅》(伦敦:Little, Brown出版社,1999年),以及Patrick French,《西藏:失落土地的个人史》(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3年)。
Matthieu Ricard与他的父亲、哲学家Jean-François Revel在加德满都的一家茶馆里进行了一周的对话。他们未经编辑的讨论是了解藏传佛教道路的最佳入门之一。见:Jean-François Revel和Matthieu Ricard,《僧侣与哲学家:父子对话中的东西方相遇》(伦敦:Thorsons出版社,1999年)。另见:Matthieu Ricard和Trinh Xuan Thuan,《量子与莲花:科学与佛教相遇前沿之旅》(纽约:Three Rivers Press出版社,1999年),以及Matthieu Ricard的以下著作:《幸福:培养人生最重要技能指南》(纽约:Little, Brown出版社,2007年);《静止之旅:来自喜马拉雅山隐居所》(伦敦:Thames & Hudson出版社,2008年);《西藏:内心之旅》(伦敦:Thames & Hudson出版社,2007年);《开悟之旅:西藏精神导师钦哲仁波切的生活与世界》(纽约:Aperture出版社,1996年);以及《不丹:宁静之地》(伦敦:Thames & Hudson出版社,2009年)。
关于肯尼亚北部游牧民族的困境,见:Elliot Fratkin和Eric Abella Roth编,《游牧民定居时:马萨比特地区游牧定居的社会、健康和经济后果》,肯尼亚(纽约:Springer出版社,2005年);Carolyn Lesorogol,《争夺公地:肯尼亚游牧土地的私有化》(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8年)。关于一本美丽且信息丰富的图册,见:Nigel Pavitt,《桑布鲁》(纽约:Henry Holt出版社,1991年)。另见我在《世界边缘的光》(温哥华:Douglas & McIntyre出版社,2007年)中的讨论。
关于文化崩溃后果的精辟视角,见:Robert Kaplan的《地球的尽头:从多哥到土库曼斯坦,从伊朗到柬埔寨,无政府状态前沿之旅》(纽约:Vintage出版社,1997年),以及《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粉碎后冷战梦想》(纽约:Vintage出版社,2001年)。另见:John Bodley的《进步的受害者》第5版(兰哈姆,马里兰州:Altamira Press出版社,2008年),以及《人类学与当代人类问题》第5版(兰哈姆,马里兰州:Altamira Press出版社,2008年)。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暴行,见:Bob Herbert,“隐形战争”,《纽约时报》(2009年2月21日),A17版。
当然,关于北极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如果要我推荐三本书,那就是:Pierre Berton,《北极圣杯:西北航道与北极探索,1818-1909》(吉尔福德,康涅狄格州:Lyons Press出版社,2000年);Hugh Brody,《北极生活:加拿大北方的猎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Gretel Erhlich,《这片寒冷天堂:格陵兰的七个季节》(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2003年)。关于Peter Freuchen,见他的《北极冒险:我在冰冻北方的生活》(吉尔福德,康涅狄格州:Lyons Press出版社,2002年),以及《爱斯基摩人之书》(伦敦:Bramhall House出版社,1961年)。另见我的文章”北方冰雪猎人”,载于《云豹》(温哥华:Douglas & McIntyre出版社,1998年),第31-55页。
关于气候变化后果,特别是冰川消退方面的两本杰出著作,见:Ben Orlove、Ellen Wiegandt和Brian Luckman编,《黯然的山峰:冰川消退、科学与社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Gary Braasch,《烈火中的地球:全球变暖如何改变世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见:Thom Hartmann,《远古阳光的最后时光》(纽约:Three Rivers Press出版社,2004年)。关于恒河的困境,见:Emily Wax,“全球变暖威胁神圣河流”,《华盛顿邮报》(2007年6月17日),A14版。关于阿马尔纳特洞穴石笋的消失,见:“神圣石笋经受不住高温”,Guardian新闻社报道,《环球邮报》(2007年7月3日),L5版。关于北美西部的昆虫侵扰,见:Jim Robbins,“树皮甲虫扩散杀死西部数百万英亩树木”,《纽约时报》(2008年11月18日),D3版。
关于撒哈拉、廷巴克图和前往陶德尼的盐商队精彩记述,请参见:Michael Benanav, Men of Salt: Across the Sahara with the Caravan of White Gold (Guilford, Conn.: Lyons Press, 2008); Mark Kurlansky, Salt: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alker and Co., 2002); Marq de Villiers and Sheila Hirtle, Sahara: A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Walker and Co., 2002); Mark Jenkins, To Timbuktu: A Journey Down the Niger (New York: Quill, 1998); William Langewiesche, Sahara Unveiled: A Journey Across the Deser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关于最终的希望愿景,请参见托马斯·贝里神父的作品,特别是 The Dream of the Earth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8); Evening Thoughts: Reflecting on Earth as Sacred Community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2006); 以及 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99).
致谢
我要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他们为激发这些讲座的探险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地理学会(NGS),我要感谢Terry Garcia和他在任务项目团队的成员,Susan Reeve, Jim Bullard, Lynn Cutter, Greg McGruder, Deborah Benson, Mark Bauman以及Oliver Payne, Tim Kelly, Chris Leidel, Terry Adamson, John Fahey, John Rasmus, Keith Bellows和Spencer Wells。电影系列 Light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起源于多伦多的国家地理频道(加拿大)和90th Parallel Productions,与国家地理频道(国际)合作制作。感谢Gordon Henderson, Cindy Witten, Stephen Hunter, Martha Conboy,特别是Sydney Suissa和Andrew Gregg,他们执导了全部四部电影。Andy和我曾在CBC传记节目Life and Times的一集中合作过。基于我的书 Light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制作更长系列的想法就是从那个项目中产生的,这成就了一次精彩的合作。感谢Rick Boston, Wade Carson, Paul Freer, Mike Josselyn, Geoff Matheson, Sanjay Mehta和John Tran在现场和录音室的出色工作。
在尼泊尔,感谢Tsetsam Ani, Sherab Barma, Thomas Kelly, Matthieu Ricard, Trulshik Rinpoche,特别是Carroll Dunham。在北极,感谢伊格卢利克和卡纳克的人民,特别是John Arnatsiaq, Jens Danielsen, Graham Dickson, Gretel Ehrlich, Theo Ikummaq, Olayuk和Martha Narqitarvik。NGS的Lori Dynan向我介绍了Nainoa Thompson和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特别感谢Lori和Nainoa以及Ka’iulani Murphy, Tava Taupu, Jeffrey Omai和Mau Piailug。关于拉帕努伊的指导和洞察,我要感谢我的朋友Claudio Cristino, Alexandra Edwards, Edmundo Edwards和Patricia Vargas。在秘鲁,Johan Reinhard和Nilda Callañaupa分享了他们独特的经验和知识。我认识他们俩很多年了,一如既往,与他们一起工作很愉快。
为了支持第二系列电影,国家地理电视台为国家地理频道制作的另外四小时节目,我要感谢Stephen Hunter和Sydney Suissa,以及Marie Wiljanen, Victoria Kirker, Cherry Yates, Korin Anderson, Tobias Louie, Nicole Teusch, Carrie Regan,特别是John Mernit和他在NG电视台的整个团队。能够与三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合作是一种特权:在内华达山脉的Graham Townsley,在澳大利亚Part2Pictures的David Shadrack Smith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在蒙古和哥伦比亚西北亚马逊地区的Howard Reid。同时感谢Jim Cricchi, Cindy D’Agostino, Robert Neufeld, Emmanuel Mairesse和Dan Marks。
在日本,我要感谢Gaynor Sekimori,她为我打开了通往天台宗僧侣和修验道丰富传统的大门。Werner Wilbert向我介绍了奥里诺科三角洲的Winikina Warao人。我与Peter von Puttkamer一起前往瓦哈卡州的马萨特克人、新墨西哥州的纳瓦霍人,以及厄瓜多尔的科凡人,在那里Randy Borman非常友善地接待了我们。Charles Lindsay向我介绍了西伯鲁特岛的门塔威人。在蒙古,我有幸与Dalanbayor, Jendupdorj, Mukhdalai及其家人, Lama Pasang Suren, Lama Lusang Ravjam, Namjin及其家人, Thomas Kelly, Carroll Dunham, Alfonse Roy, Nandu Kumar和Bat Amgalan Lhagvajav合作。
在哥伦比亚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感谢Jaime Andres Cujaban, Ramon Gill, Roberto Mojica, Peter Diaz Porta, Alfonse Roy, Eugenio Villafaña, Danilo Villafaña和Rogelio Mejia,以及正式欢迎我们合作的许多土著组织:Bunkwanarrua Tayrona, Organización Gonavindua Tayrona, Organización Wiwa Yugumaian, Organización Indígena Kankwama, Confederación Indígena Tayrona。
在澳大利亚,Carrie Williamson向我们介绍了Adam McFie,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他反过来把我们带入了Otto Bulmaniya Campion和他的妻子Christine及其美好家庭的世界,以及Peter Djigirr, Peter Girrikirri, Richard Bandalil。同时感谢Ramingining护林员, Lindsay Wile, Jeremy Ashton, Ray Whear和Jawoyn协会,以及人类学家Bob Tonkinson的建议和指导。
在巴拉萨纳人和他们邻居中度过的时光,得以实现要感谢哥伦比亚驻美国大使Carolina Barco及其同事Denisse Yanovich、Mercede Hannabergh de Uribe和Edgar Ceballos将军。与皮拉帕拉纳土著首领协会(ACAIPI)以及皮拉帕拉河流域人民的合作,得以实现要感谢我的好友Martin von Hildebrand及其在亚马逊盖亚基金会的同事们,包括Nelson Ortiz、Silvia Gomez、Natalia Hernández和Jorge Kahi。在野外我们与人类学家Stephen Hugh-Jones一起,他以极大的慷慨精神分享了他通过毕生对这片土地的深入钻研所获得的深刻知识。一路上,我们在具有非凡深度、洞察力和敏感性的巴拉萨纳和马库纳学者的指导下前行:Maximiliano García、Roberto Marín、Ricardo Marín、Rosa Marín、Reinel Ortega。我们的团队Ryan Hill、Peter Diaz Porta、Yesid Ricardo Vasquez和Diana Rico,都很愉快,与他们合作很愉快。还要感谢ACAIPI以及河流沿岸的所有社区和人民。
在这些讲座结尾简要描述的撒哈拉之旅,得以实现要感谢Roberto Cerea及其在TransAfrica的杰出团队。与我们一起参加那次冒险并分享他们智慧的有Alex和Caroline Chadwick、Isa Mohamed、Baba Omar和Salem Ould教授。在东非,Kevin Smith和Jonathan Lengalen为我做向导。在砂拉越,我要感谢所有本南人及其支持者,尤其是Lejeng Kusin、Anderson Mutang Urud、Asik Nyelit、Tu’o Pejuman和Mutang Tu’o、Ian MacKenzie、Bruno Manser和Peter Brosius。
对于其他一切,所有这些让这些冒险成为可能的友谊,许多为我提供家园、归宿的人们,我想要感谢Darlene和Jeff Anderson、Monty和Pashan Bassett、Tom Buri、Natalie Charlton、Lavinia Currier、Simon和Cindy Davies、Oscar Dennis、Lindsay和Patti Eberts、Clayton和Caryl Eshleman、Stephen Ferry、Guujaaw、Peter Jakesta、Sven Lindblad、Barbara和Greg MacGillivray、Peter Matson、David Maybury-Lewis、Frederico Medem、Richard Nault、Richard Overstall、Tim Plowman、Travis Price、Rhoda Quock、Tom Rafael、Chris Rainier、Gerardo Reichel-Dolmatoff、Richard Evans Schultes、Dan Taylor、Kevin Smith、Peter和Sheera von Puttkamer、Tim Ward,以及Leo和Angie Wells。
在CBC,我要感谢Philip Coulter和Bernie Lucht。在Anansi出版社,我要感谢Lynn Henry,一位出色的编辑,以及Sarah MacLachlan、Laura Repas、Janie Yoon,和Bill Douglas的封面设计。
一如既往,最后的感谢献给我的姐姐Karen和我亲爱的家人,Gail、Tara和Raina。
《偿还》 Margaret Atwood ISBN 978-0-88784-810-0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72-8
《更多遗失的马西讲座》 Bernie Lucht, 编 ISBN 978-0-88784-801-8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66-7
《词语之城》 Alberto Manguel ISBN 978-0-88784-763-9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49-0
《遗失的马西讲座》 Bernie Lucht, 编 ISBN 978-0-88784-217-7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64-3
《伦理想象》 Margaret Somerville ISBN 978-0-88784-747-9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83-4
《与时间赛跑》 Stephen Lewis ISBN 978-0-88784-753-0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75-9
《进步简史》 Ronald Wright ISBN 978-0-88784-706-6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43-8
《故事的真相》 Thomas King ISBN 978-0-88784-696-0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95-7
《超越命运》 Margaret Visser ISBN 978-0-88784-679-3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46-9
《效率崇拜》 Janice Gross Stein ISBN 978-0-88784-678-6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80-3
《权利革命》 Michael Ignatieff ISBN 978-0-88784-762-2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92-6
《叙事的胜利》 Robert Fulford ISBN 978-0-88784-645-8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94-0
《成为人类》 Jean Vanier ISBN 978-0-88784-809-4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45-2
《别处社区》 Hugh Kenner ISBN 978-0-88784-607-6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82-7
《无意识文明》 John Ralston Saul ISBN 978-0-88784-731-8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96-4
《千禧年前夕》 Conor Cruise O’Brien ISBN 978-0-88784-559-8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70-4
《民主受审》 Jean Bethke Elshtain ISBN 978-0-88784-545-1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54-4
《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 Robert Heilbroner ISBN 978-0-88784-534-5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97-1
《现代性的不安》 Charles Taylor ISBN 978-0-88784-520-8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86-5
《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 R. C. Lewontin ISBN 978-0-88784-518-5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47-6
《技术的真实世界》 Ursula Franklin ISBN 78-0-88784-636-6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91-9
《必要的幻象》 Noam Chomsky ISBN 978-0-88784-574-1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68-1
《同情与团结》 Gregory Baum ISBN 978-0-88784-532-1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51-3
《我们选择居住的监狱》 Doris Lessing ISBN 978-0-88784-521-5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74-2
《拉丁美洲》 Carlos Fuentes ISBN 978-0-88784-665-6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62-9
《对绝对的怀旧》 George Steiner ISBN 978-0-88784-594-9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69-8
《设计自由》 Stafford Beer ISBN 978-0-88784-547-5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55-1
《家庭政治学》 R. D. Laing ISBN 78-0-88784-546-8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89-6
《民主的真实世界》 C. B. Macpherson ISBN 978-0-88784-530-7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90-2
《有教养的想象》 Northrop Frye ISBN 78-0-88784-598-7 电子书ISBN 978-0-88784-881-0
在优秀书店及 www.anansi.ca 有售
House of Anansi Press成立于1967年,旨在出版加拿大作者的书籍,这一使命延续至今,尽管出版目录已扩展到包括国际知名的思想家和作家。该出版社因出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迈克尔·翁达杰、乔治·格兰特和诺斯罗普·弗莱等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而立即获得关注。从那时起,Anansi致力于发现、出版和推广具有挑战性的优秀作品,为其赢得了巨大的赞誉和稳固的持续力。如今,Anansi是加拿大最杰出的独立出版社,是吉尔·亚当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肯·巴布斯托克、彼得·贝伦斯、拉维·哈格、米沙·格伦尼、吉姆·哈里森、A.L.肯尼迪、帕夏·马拉、丽莎·摩尔、A.F.莫里茨、埃里克·西布林、卡伦·索利和罗纳德·赖特等全国和国际畅销书及备受赞誉作家的家园。Anansi还自豪地出版获奖的非小说类系列《CBC马西讲座》。2007年和2009年,Anansi被加拿大书商协会授予”年度出版商”荣誉。